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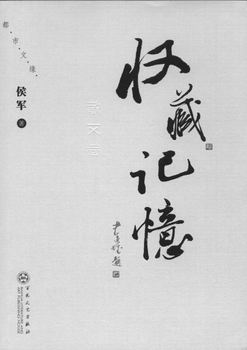
假如读过一本书能够记住某些片断,让人在新奇的称许中久久玩味,并由此而记住了作者,认识了作者,那么,这本书肯定是有价值的。我的这个感觉,在读了侯军新近出版的艺术评论集《读画随笔》和散文集《收藏记忆》两本书之后,似乎又有了新的认知和佐证。早在20年前,孙犁读了尚不知名的侯军的一封信和一篇评论提纲,就不惜笔墨,复信予以肯定,称许他“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的精神。那是夕阳对朝阳的召唤,比我们普通人的感觉深了一个层次,具有指导和激励的意义。从那时起,侯军遵循大师的指点,一步步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于浮躁的世风中抱定操守,奋力笔耕。这两本书,应视为寂寞的精神之树上结出的最新果实。
《读画随笔》和《收藏记忆》两本书,实际上是一本书,是艺术的青鸟展开的双翼。翻开书页,你会不由自主地走进瑰丽无比的艺术的殿堂。这里画廊曲回,幽深古远,两侧东西方绘画琳琅满目,相映生辉。作者仿佛一个资深的导游,为你讲述东西方绘画史上的星座对应、作品比较、艺术渊源、理念异同。他“既无条条框框,又无门派壁垒,全凭着对绘画的知觉和对艺术的喜爱,发表对美术的看法”(作者语)。这种讲述,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率性而为,随感而发”的,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对史的纵深洞察和研究,没有对现实的美术情状的关照和思索,《读画随笔》开篇的几篇大文如《打开画卷看千年》、《从摈弃传统到古典复归》、《中国绘画传统的现代诠释》、《日本浮世绘与中国木版年画》等,是不会写得如此文采斐然如此具有学术意蕴的。侯军说画,决非就画论画,他是从社会的、历史的、文学与哲学的角度,把对象置于大背景下,进行人文的透视,比较的研究,于是才有了达芬奇与唐伯虎遥相感应,勃郎宁与八大山人的心志趋同,东西方绘画的对立统一,古典派与现代派的殊途同归。从艺术的创作方法上看,这种揭示等于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包括它的各种派别)不过是人类生活的沃野上,一棵大树的几条枝桠,它们共同支撑着艺术的蓊郁与繁荣。
我的这种解读不知是否游离了作者的本意,但它至少说明,侯军的艺术探索,早已跳出了绘画、书法、雕塑的领域,从而具有了普遍性的品格。20世纪末叶,中国的大门刚刚开放,西方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风涌而至,冲开了封闭了几十年的门扉,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掀起了追新求异的波澜。文学、艺术进入了新时期。然而随之而来的,一股民族虚无主义的罡风也搅起浊尘黄沙,令人莫衷一是。在绘画界,则有否定传统、否定国画的波流涌动。侯军对此持清醒的反对态度。但他不愿以简单的指斥为武器,而是用学术的辨析的方法,给予中国传统绘画、书法以现代诠释,找到东西方文化艺术观念的交汇点,使那些对老祖宗妄自菲薄、自暴自弃的人们,感到自己的偏狭和无知了,使那些迷茫的人们大吃一惊:呦,我们的国画并不落后,它的传统精神正迸发着现代意识的光芒。扩而言之,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门类,情况不也是这样吗?遗憾的是,在文学方面,我还没见到哪一位学者作侯军式的比较研究,这是不应该的。
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知它。或许正是由于对东西方绘画的深刻认识,侯军才对中国画有所偏爱。这种偏爱,驱动着他的脚步,去探求国画的真谛,去结交画苑的先贤,去晤识当代的名流,去采撷缤纷的花瓣,品画记人,钩沉翻新,显示出学者型记者的游刃有余和作家型报人的文字功力。在他的笔下,范曾的飘逸超群,王学仲的满纸云烟,钱绍武的谦和内敛,华非的深谙禅机,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根植于心灵深处,难以忘怀。他品画兼及品人,滋滋有味;写人诗画并举,底蕴丰厚。他尤其擅长撷取人物的情景妙语,常常只几个字,便如闪烁的星星照亮了人们的眼睛。请看《笔烛》的最后一段:
一日,宁公(书法家宁书伦―――笔者注)于作书之后,取过一支毛笔,笔尖向上,举到跟前,问我:“你说,这像什么?”我说:“像个锥子。”宁公摇头。我又答:“像个塔尖。”宁公依然摇头。我反问:“你说像什么?”
“像支蜡烛。”宁公答道,“书家的笔,就像一支笔烛,那笔中的墨,就像是烛泪,――蜡炬成灰泪始干啊!“
这一幕,不但是作者,任谁也会怦然心动的。“笔烛”之妙,不仅在于它比喻的精确,还在于它诗意的表达。人们据此可以联想,书家的笔,流淌的不是墨,而是生命的追求,感情的泉涌,而那落在宣纸上的字,就不单是语言的符号,而是书家意趣心志的挥洒了。笔烛,笔烛!燃烧的是自己的躯体,升腾的是太阳的光焰。宁书伦的一生岁月,就在这两个字里了。这是何等的简洁,又是何等的丰腴。侯军的笔也是一支烛。
他用这支笔烛写下大量的艺术随笔,同样,他也用这支笔烛写下大量的诗意的散文。《草龟祭》写一只善解人意的草龟,受了意外的损伤,上小学的女儿为此写了一篇情真意挚的作文。念给它听的时候,它竟“一动不动,一副全神贯注的模样;一旦念完,它立即挪动地方,像是听到了下课的铃声一样”。可是换个人念,它便充耳不闻了。女儿于是就更加喜欢它。也许是那次损伤太重了,它的体质每况愈下,当听说要把它放生时,竟在送它走的前一天晚上死了。大家都很伤心,女儿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她为小乌龟选好墓地,还写了祭文。故事至此,已经很感人了,但作者笔锋一转,将我们引进人际关系的境地:“一个寻常生命,能够在其生时为别人带来快乐,死后还能为人们所怀念,这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即使是人,也很难说都能做到这一点。”这种以“不类为类”,是深得诗人心手之妙的。古人写诗,讲究“诗眼”,于山重水复之中,达到柳暗花明之境。好的散文,也应以诗为骨,于平淡中现出奇崛,于叙事中升华感悟。《草龟祭》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具有直抵人的心灵深处的力量。他的直接写人的散文,则偏重揭示其内在气质和性格特征,常常选取一件小事,或者截取一个生活细节,便画出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来。怀念孙犁先生的文字,有这么一段:孙犁病重之际,我和滕云去看他。老人话不多,但看上去心情很好,只是滕云说到天津日报五十周年庆典,本想请先生写几个字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孙犁先生像听见了刺耳的防空警报似的,立即大声说道:“写不了,写不了啦!”后来,我说一些在南方怀念老人的话,老人平静而友善地听着,可当我一说起大家都希望看到您写出好作品时,“老人就不再应声,慢慢地把眼睛闭上了。”孙犁先生一生以“写”为业,却在弥留之际,闻“写”而惧,这是怎样一种心境啊!其实,这正是先生真率心性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在他笔健时,谁不言写他会不开心;在他不能写时,谁再言写他会视为一种虚礼。侯军的其他写人物的篇什,也大都从大处落墨,小处精雕,人物便跃然纸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