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的名字是和《井冈翠竹》一起深深印入我脑海的。多年之后,我参加工作走进人民日报文艺部,在部里的新年茶话会上,来了一位胖胖的、和蔼的仁厚长者,同事们叫他“老田”。这就是袁鹰,他的本名是田钟洛。著名作家袁鹰和文艺部主任老田,到这时才重叠在一起。
几年前,袁鹰先生的《两栖人语》出版后,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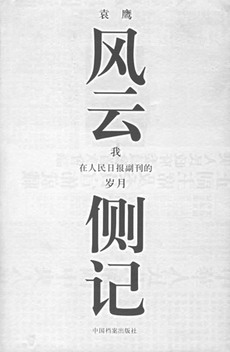
作为一位过来人,袁鹰的这些回忆文字中,多了一份澹定,少了一些抱怨;多了一份反思,少了一些激愤;多了一份忏悔,少了一些辨白。这是穿透历史风云的文字,是穿透个人恩怨的文字,但是透过这些澹定的文字,我更深地读懂了当年的隐隐风雷,读懂了那一代人的不幸。
首先,撇开十年浩劫不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艺战线上刀光剑影,寒气逼人,一个小小的文艺问题动辄上纲上线,或把人打成反革命,吓得众人噤若寒蝉,文艺园地日见荒芜。从批《武训传》开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文艺界人士普遍感到脑袋上顶着一颗雷,不可能放开手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
其次,如此过度重视文艺的舆论氛围,造成了“歌德”文字盛行,说真话倒霉的现实。这部书中,牵涉到杂文的篇章占了不小的比例,从胡乔木、夏衍等人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到1957年的“丁酉之难”,1962年杂文栏目《长短录》的夭折,一直到赵丹的遗言,我们发现由鲁迅先生开创的现代杂文尽管一直被奉为经典,但真正的鲁迅风杂文带给作者、编者的只有灾难。不仅一大批杂文作者,像邓拓、巴人、吴祖光、邵燕祥等先后罹难,编杂文的陈笑雨、袁鹰等人也备尝苦果,陈笑雨竟至自溺身亡。事过多年,袁鹰先生痛定思痛,剀切陈辞:“说长道短,本来就应该是舆论的天职,是舆论为社会、为国家、为广大读者应尽的责任。”“如果从上到下,大家沉醉于虚假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生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满足于莺歌燕舞的升平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严重的失职吗?”袁鹰先生问得好,可是他赶上了那样一个不敢说真话的时代,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大不幸。
人是不可能选择时代的,时代可遇而不可求,这是人的命;但生在一个时代,不管它好也罢歹也罢,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影响、改变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这是人的运。袁鹰赶上那样一个幸或不幸的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管做弄潮儿还是吹鼓手,都坚持了自己的书生意气和文人品格,为周围的人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小环境,就凭这一点,他有理由赢得我等晚辈更多的敬重。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