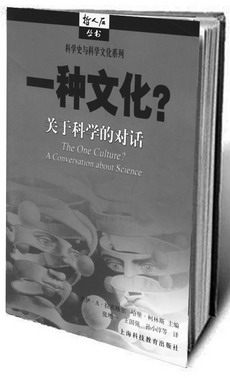
题目中第一个“堪”的意思是“能忍受”,第二个“勘”的意思是“实地查看”、“调查、查问”。《红楼梦》中有“勘破三春景不长
文人关注科学凸显时代文化矛盾
这里的“不堪”涉及到两方面的意思:(1)科学(界)是否有雅量,主观上能否摆出一种姿态任凭他人点评?(2)科学(界)自身是否经得起他人的详细考察、审视。这是我读《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一书首先想到的两个问题。
前者涉及自然科学共同体在“两种文化”之争或“科学大战”中是否足够自信、是否尊重对手、是否愿意倾听非科学领域的意见。后者涉及从客观效果上看,当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和运作过程是否如早先描述或者许诺的那样完美、可爱。
《一种文化?》是一部很特别的多人文集,主要内容是展示双方(“科学实践者”和“科学评论者”。其实是多方,每个人的具体见解也有差别)关于科学大战的真诚对话。本书的主编一位是科学家拉宾格尔(J.A.Labinger),一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学者柯林斯(H.Collins)。到现在,我们不知道多数科学家究竟怎样看待“自然科学观”在过去几十年里不可逆的转变过程。拉宾格尔这样的科学家(估计是少数)确实是值得称赞的,他重视对手、尊重对手,能够通过阅读、倾听、交谈、书写,来阐述自己的科学观,努力增进科学与人文的相互理解。对称的一面几乎不用提起,因为据我所知,多数SSK学者,是高度重视自然科学的,认真对待自然科学的,甚至比科学家本人还认真。
“科学大战”为何如此“显眼”、具有冲击力?两种文化的传统早就有,从来就不曾间断过。冲突为何偏偏在1996年前后达到一个高潮?仅仅因为爱丁堡、巴斯和巴黎的几个社会学家以及部分后现代学人对科学怀有敌意,或者媒体闲来无事对知识分子“爆料”?稍想一下便会发现,这种冲突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全球问题和文化矛盾的一种反映,不是个别学人或好事的大众传媒能够炒热的。
“科学元勘”职业化过程揭示“圣殿”神话
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这三大本来就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20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就已存在,已经对科学事物说这说那。但它们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前,对庞大、强大、自大的自然科学界,根本不构成威胁、不会令科学伤筋动骨(其实现在也没有,只是有人感觉如此),相反这一时期这三个学科基本上充当科学赞美者的角色。“在1960年代之前,这些研究领域中很少有东西会引起职业科学家群体的冲突。相当一部分科学史是由退休的或怀有多种爱好的科学家们自己写成的,而且更多的带有赞美性质。”“科学哲学的研究只是想要解释科学为什么会成功,而不是要对科学世界观提出挑战,因而科学家们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冒犯之处。”“默顿[科学]社会学里的东西绝对不全是赞同科学家的自我形象,但总的来说重点在于解释这些建制如何使科学家把工作做得如此漂亮。”(《一种文化?》,第4页)这一派的科学社会学当然也不构成威胁,相反他们还颇受欢迎,默顿本人竟然得到了总统科学奖,科学社会学出身的加菲尔德搞的SCI更令大科学如火如荼。总之,这三个学科的研究对于科学是安全的。
但是,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忽略了这三个学科缓慢的演变过程及其科学对其态度的微妙变化,事实上“科学元勘”也在职业化,只是比科学的职业化晚一拍而已。当科学哲学深入到关于科学事实、科学推理、因果性的细节讨论时,科学家出身的业余哲学爱好者已经显得不耐烦,觉得科学哲学无趣、与科学无关。比如温伯格引用据说是费恩曼的话说:“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就像鸟类学对于鸟一样,毫无用处。”(《一种文化?》,第4页)可是又过了一些时间,当SSK兴起、科学大战爆发时,同样是这位大科学家,已经由“无关论”变成了“威胁论”,他看到了由无知的民众和同样无知并带有敌意的人文学者控制的社会民主过程可能给自己坚定捍卫的自然科学带来伤害,当SSC(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被美国国会否定,温伯格等科学家像祥林嫂一样唠叨个没完。他一方面承认自己在SSC项目上“没有任何专门知识”,一方面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SSC项目,却提不出像样的理由。他终于想出一条安抚其他反对SSC的科学家的假定,一旦上了SSC,对整个大科学都有好处,没准儿大家都会额外分到一些经费,“有助于普遍增拨研究经费”。(《仰望苍穹》,第19页,第34页)到了90年代中期,温伯格则再也忍不住,要与SSK学者直接战斗了。虽然他是一流的科学家,对科学的刻画却无论如何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他曾武断地说:“即使科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共识,它也不像任何其他种类的共识那样,因为它是不受文化影响的,而且是长期不变的。”(《仰望苍穹》,第110页)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发展得更有反思性,对科学的微观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推翻了科学与社会、文化无关的大神话。
如今这三个学科都受到建构论的严重“侵蚀”,在科学共同体看来,科学在学者面前的形象以及科学的公众形象可能受损,本能的反应是把人文学者当成大战的敌方。“隐藏在科学大战背后的十字军骑士们,决不想把给钱的人扔出科学的圣殿。”“他们的复仇枪口瞄准那些证明该圣殿是怎么被建立起来,其祭仪又是怎么维持下来的人,即建构主义的学术左派。”(《科学大战》,第13页)
谁企图垄断理性?
“科学大战”与其他战争一样,责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但是对战争的评判要考虑到正义性、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可能的后果。科学大战是谁挑起的?争论双方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高级迷信》和索克尔事件,显然是来自科学界的蓄意挑衅。“索克尔发出了我们内心的呼声,让我们同他一样感到兴奋。”(《一种文化?》,第269页)“片刻之间”,科学家觉得好像赢得了胜利。科学界一度企图暗示,部分人文学者是科学残废或低能儿,没有资格对精致的自然科学说三道四。好在,《一种文化?》这部书中的科学家没有这样设想对手。其实,即使SSK等学者对某科学科不太在行(通常很在行),二阶的探讨依然是可能的、合法的。道理很简单,好比张艺谋拍摄了一部《科学大传》,刘兵对电影进行了一番评论。张导演没有理由指责刘兵不会拍电影,刘兵只需说我对电影有自己的理解,这与我本人是否会演戏是否懂得光圈、道具、布景、剪辑基本无关。一部电影,即使是天大的大片,对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影响也有限,而科学则不同。“致毁知识”、转基因作物、克隆人等涉及到几乎所有人的利益。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SSK等学者是讲道理的,他们的评论,基本上不是在批判、诋毁,而是在勘察、分析。因而SSK学者不是反科学、反理性,其对手倒是有点像――但这种指责不会由SSK学者主动发出,因为他们深得建构的要义。捍卫“科学”的尊严,不但科学家在做,SSK学者也在做,但他们的工作处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空尺度。
强大的科学(包括其目标、运作、成果、价值观)应当是耐勘破的、抗冲击的。如果某些“科学”不堪一勘,那么这些科学也该自我反省一下了。鸟类学对鸟来说也许没什么用处,但是人类对某种鸟的看法,绝对关乎鸟的命运。
又及:我怀疑两位主编书中的总结过于乐观,忽略了双方根深蒂固的分歧。夸大和忽略鸿沟都是危险的。
《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美]拉宾格尔、[英]柯林斯主编,张增一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34.00元
相关阅读
《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敌手》,[美]温伯格著,黄艳华、江向东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20.50元
《科学大战》,[美]罗斯主编,夏侯炳、郭伦娜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2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