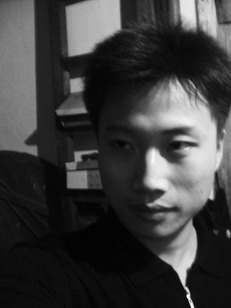
可是我所眼见的“现状”就是这么无聊,无聊得都滋生出一点诗意来了。行动的周转于我们而言,可不是尽遵循着付钱找零那么简单的规律?然而我没有告诉他,阿米亥还有上文:“一间屋里三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总是伫立在窗前。/被迫观看荆棘丛中的不公,/山上燃烧的火。”这个伫立的人也许就担当着打破寂静的使命,哪怕是被迫的,偶然的。就像几个月前,我在阿米亥的同胞阿莫斯・奥兹的小说里看到的那种情景:一对上了年岁的情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迤逦投入到一场公益活动的酝酿之中。
不读奥兹,还真想象不到他所在的这个裂缝形的国家会有像特尔科达那样宁静的角落。在《莫称之为夜晚》(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4月版)里,奥兹广有口碑的诗意叙事表现于对现状的重复描写,构成特尔科达的“现实”的是这样一些画面:站柜台的鞋店老板,天天出神地怀念他那死于失恋士兵扫射的妻儿;一对新婚夫妇永远站在家居店里,因审美品位不同而争论不休;一位双目失明的老职员每天早晨在公园长凳上静坐,起身时偶尔绊在导盲犬的身上就赶紧赔不是。就像RPG游戏里的布景,人们始终处于自己的位置上,保持同样的姿势,说着同样的话。
特尔科达的地理环境就给人以恒量的静止感,它的每条道路都通往城外的沙漠,市容牵连着它的历史和记忆细节,始终维持着一成不变的形貌。但在以色列,这种静止,以及主角们对内心宁静的追求,往往只是徒然的表象。在1994年发表的这部作品中,特尔科达正处于两场风暴之间短暂的宁静期,人民没有忘记危险,只是因为地处偏远,他们的反应只能限于发几句牢骚,限于在庭间挂几张锡安主义领袖的画像。但在市中心的欧文・科西查广场上矗立着一座纪念“覆没的勇士”的碑,碑上铭刻着几个金属字:“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杀”,倒数第二个字别有用心地灭失了,透出宿命的暗示。这时,一个名叫伊曼纽尔的男孩在失踪多日后,被人发现死于悬崖之下,据传死因是吸毒,于是他的父亲阿弗拉翰・奥维耶多发起动议,要捐款在特尔科达成立青少年戒毒所,45岁的诺娅,男孩的老师,被他请为义举的牵头组织者。决心一下,诺娅和年长他15岁的情人西奥之间,一波波掀起了无声的震荡。
奥兹叙事的宁静感糅合了凄美和寡淡:凄美很大程度上来自沙漠和群山的环抱,而寡淡则是凡人度日的常态。不过,就连拒绝提供帮助的官员也没有忘记以色列的昨日,“那时候的国家还只有沙丘和梦想呢”――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就在为梦想而战,其中不乏西奥这样背着炸弹冲向英国警察局,把雷达设备轰上天的好汉。正如奥兹在1976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说《鬼使山庄》(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6月版)中描写的那样,在阿拉伯力量拒绝依联合国指示,与以色列和平分治的时候,就连三尺蒙童都在朝思暮想着光复家园。一位名叫尤里的犹太小男孩,发现大人们都在为民族复性的伟大事业而密谋,于是也把自己想象成了民族伟人的助手,想象自己不卑不亢、视死如归的画面。复国主义运动本身恐怕谈不上正义邪恶,只是那种全民共有的积极一致的热望足以激动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诺娅的潜意识里也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手头的事与更大的梦想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一位无从参与政治的弱女子也分享到民族激情的一部分,她也需要某种可以投入进去的“事业”。
我把奥兹这两部小说列为年度最佳文学作品,除了其悠扬耽美的叙事之外,更是因为我喜欢这位作家刻画的一种因庸常而不安、进而思变的民族品质,它使得故事情节暗流涌动,密布内在的紧张。这是一群总有事儿要干,总有问题要讨论的人,即便素昧平生,人的思虑、关怀和抱负也能指向一种高度的认同,这种认同当年促使他们联手在沙丘上建筑梦想,尤里的父母、邻居及其同志,各路神秘的来客,都在为梦想而密谋;而后来诺娅遭到的种种冷遇,则折射出民族传统面临代际更迭的必然考验。
犹太人好像一个站了大半天,终于觅到一个有争议座位的乘客,即便成功地坐下也脱不了紧张,不停地揣度着民族的分量和前途――这是《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两届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十多年前的妙喻。美国大作家索尔・贝娄70年代末访问耶路撒冷,在访问记里失声感叹:这里的高度现代化与其公众的社会积极性并行不悖,无数市民在设施一流的餐厅里讨论民族和城市的未来。这位乘客占座的正当性大可理论一番,然而,此人兼备的宁静与兴奋,对危机的自发自觉,就像内盖夫沙漠的河流一样匍匐潜隐,莫测高深,给人以威胁抑或希望。
诺娅最担忧西奥失去这种自觉,他似乎不再是当初的义士,也不再是诺娅八年前认识时的那位精力充沛的城镇规划师了。他好像成了一名寂静主义者,他用凉飕飕的现实主义腔调不断给诺娅泼冷水:投资能否到位?能通过政府审批否?把全以色列的不良少年都集中到这里,这片犯罪率极低的荒漠小城,怎么跟邻居交待?诺娅不愿接受这种事实:庸常俗务制约了事关公益的理想付诸实施;满足于庸常的寂静主义者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兴奋,他只需服从各种规则的简单分配,在市场给出的选项里择一而从以塑造自己的生活:如此得来的宁静是多么安全而又不乏明智。
寂静之魔让人融化在现状之中。在这让人心境飘零的冬季,我们自己的生活背景,那些早已嵌入市容的人与事物也正在走向寂静,仅有这样的一些的变化:支起多时的临时工棚悄悄地偃旗息鼓了,天天咆哮的摩托随跑速递的主人转投别处了,嗒嗒响了一年的麻将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相互打听才知道麻友们择他木而栖了。多少人像零钱一样在自己的各个口袋里挪来转去。寂静主义者通过传媒学会各种娱乐眼球和性器的新花样,并且懂得了用这些唾手可得的粮食填满生活的各个空隙,广采秀色投入精神层面的欲壑,向屏幕背后的世界买来扮演英雄的机会。寂静主义者不会产生共同的目的,在事关公共的问题上保持习惯性沉默;他们不会在乎集体智慧的结晶换来一人独吞的稿费,也懒得去关心关于一个人是非荣辱的评定,能在多大程度上肯定或推翻他的全部作为――因为那实在不关他们的事。只有街道里张贴的一张认尸告示,能用彩色的扭曲的脸吸引行人。不过未及数日,人脸被描了眉,画上了眼影和胡髭,貌似是从日式卡通学来的“深描”笔法。当环境冷却的时候,就连所谓的童趣都成了一种令人尴尬的嘲讽。
作家没有结束故事,但我们知道西奥最后没有让诺娅失望,戒毒所理想不论是否实现,都深化了两人的相互认识;男孩尤里则失望了,在行动之日来临的时候,生活忽然又恢复到庸常的轨道中,所有的民族英雄、救世主都没有出现:“我们还要继续等待。一切如常,新的一天开始了。”淡淡的两句话提醒读者,这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小信徒是带着怎样的不妥协归于宁静的。――没有理由羡慕犹太人的命运,更没有必要去景仰他们的英雄,那些信奉“所有与我为敌者不得入我城池”的英雄,换一个角度看也是怨怨相报的牺牲品。但是,一种能促进认同、凝聚进而行动的集体记忆或历史叙事,却是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
从阿莫斯・奥兹这里我们是得不到对策的――我们没有对应的财富,或似乎已被瓦解――我们只是受到他们处世方式和态度的深刻刺激。作为“现状”的组成部分,一间屋子的三四个人里,总得有人率先去留意着哪座山上燃烧着火,不管出于什么缘由……然后,其他人才会缓慢地关注到他,进而更慢地注意到窗外那能够射破现实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