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厨房是女人的领地。王宣一的《国宴与家宴》,讲的就是“一个家庭餐桌和厨房里的光阴的故事”。那是一个女儿深情回忆她的母亲,如何在“那样一个年代”为家庭为儿女做饭的记录。虽然作者不愿意说这本书是对母亲的怀念(“我怎能用这样微薄的书写来怀念她?”),但在我看来,一个女人在厨房的一生,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微薄”的。特别是当那个女人是一个母亲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吧,在那些生活贫瘠的年代,聪明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变着样儿的,在厨房在餐桌为孩子们制造出多少小小的奇迹、小
小的幸福啊。就拿我来说吧,我永远都忘不了母亲为我们做的,晒在竹条床上的那些亮晶晶的薯片,甜甜的在嘴里慢慢溶化的感觉。再看看《国宴与家宴》中,一个女儿记忆中的母亲,是何等的神奇吧。“我一直记得母亲晚宴旗袍,在厨房进进出出的样子。那个时代的厨房大都在屋子最畸零的角落,密闭且通风不好,可是她就是能从容悠闲地穿进钻出准备菜肴、招呼宾客,看不出一点忙乱来。”“她总有本事前一分钟在厨房忙得灰头土脸,下一分钟就轻轻松松端出一盘漂亮的菜来。富富泰泰的好像不曾经历过前面的油烟、忙乱,就做出来了。自信笃定的神情,似乎使那些菜色加倍地可口诱人。”这不是艺术是什么?这种艺术只有一个伟大女人才能创造出来。
我们从身穿“晚宴旗袍”下厨这个细节大概可以想见,王宣一的母亲许闻?女士也不是什么一般人物。书中附有一帧许闻?身穿旗袍怀抱幼时作者的小照,颇有风姿。据作者介绍,她母亲许闻?出身浙江海宁的书香世家,接受过西式教育,中日战争时跑过空袭,在战争之中,只身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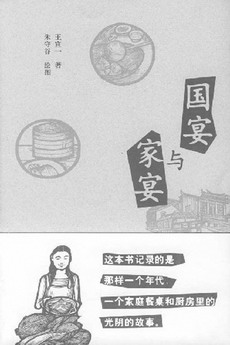
所以,《国宴与家宴》,我宁愿把它理解为一本生活之书,而不是历史之书。虽然书名《国宴与家宴》,让人不由生起“家国之想”,让人想到白先勇的《游园惊梦》。一个谈食一个谈戏,不免有兴亡之感。但是《国宴与家宴》的双重“记忆”(作者对自己童年的记忆和母亲对童年的记忆)更多是关乎个人生活的。正如作者说的,“食物和记忆的关系真是最最密不可分”,一道菜肴为什么非如此做不可,与其说是个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个人记忆问题,对童年经验的回味,是对某个人一生某个片段的重温。《国宴与家宴》在我看来,并不是谈饮食而是谈记忆。细细描述一个女人一生的烧菜做饭,学会她拿手的菜肴,我认为,算是对她最温馨最深情的记忆。一个女儿和一个母亲之间心心相通的关系莫过如此了。
《国宴与家宴》,王宣一著,朱守谷绘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