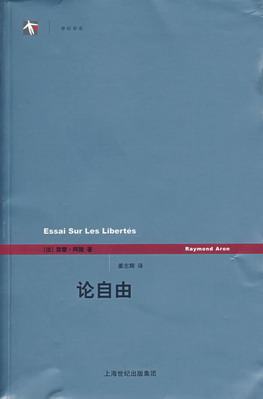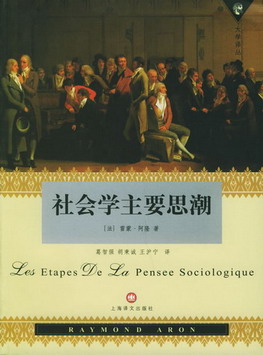如果真能静心一读,读着读着就会发现,除了思想的清晰和犀利以外,雷蒙・阿隆的“平淡无奇”中还蕴含着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我们这里不太熟悉但却引人入胜的精神气质。

1
雷蒙・阿隆是来迟了。这位在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都与萨特齐名的思想家,在我们这里却至今没有什么“知名度”。以至于要推介他的作品,第一个需回答的问题竟然是:谁是雷蒙・阿隆?于是,所有的推介者都不得不把萨特给抬出来:他是萨特的同窗好友和终生论敌,作为一面思想的旗帜与萨特比肩而立,如此等等。回想1980年代,萨特在我们这里的名头有多大?与他的名字相连的存在主义一时成为时尚话题,“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等命题也常被人们一知半解地挂在嘴边。说怪不怪,那个年代的人们相信思想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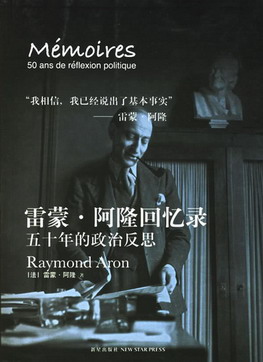 轮到雷蒙・阿隆出场时,我们这里的风气变了,人们似乎更相信利益的力量了。即使借助萨特的名头,雷蒙・阿隆也没能引起太大反响。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雷蒙・阿隆的《社会学主要思潮》中译本时,1980年代就快走到尽头。待到1992年三联书店出版《雷蒙・阿隆回忆录》时,已然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了。整个1990年代过去之后,雷蒙・阿隆其他著作的中译本如《阶级斗争》(译林出版社2002年)、《论治史》(三联书店2003年)、《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05年)等等才陆续问世。其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在小范围内有了一定影响。之后《雷蒙・阿隆回忆录》又得以重新出版(新星出版社2006年),看来雷蒙・阿隆在我们这里终于赢得了某种程度的关注。
轮到雷蒙・阿隆出场时,我们这里的风气变了,人们似乎更相信利益的力量了。即使借助萨特的名头,雷蒙・阿隆也没能引起太大反响。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雷蒙・阿隆的《社会学主要思潮》中译本时,1980年代就快走到尽头。待到1992年三联书店出版《雷蒙・阿隆回忆录》时,已然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了。整个1990年代过去之后,雷蒙・阿隆其他著作的中译本如《阶级斗争》(译林出版社2002年)、《论治史》(三联书店2003年)、《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05年)等等才陆续问世。其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在小范围内有了一定影响。之后《雷蒙・阿隆回忆录》又得以重新出版(新星出版社2006年),看来雷蒙・阿隆在我们这里终于赢得了某种程度的关注。
其实,只要读了《雷蒙・阿隆回忆录》,“谁是雷蒙・阿隆?”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只是这部回忆录长达70万字(近700页),读起来还真有点费劲。这年头的人都缺乏耐心,阅读也习惯了短平快。更何况雷蒙・阿隆的叙事“平淡无奇”(据说他常用这个词来表达一种赞赏的意思!),绝少抑扬顿挫。要按我们这里相传已久的文人标准,怎么着说他也是“略输文采”的。不过,如果真能静心一读,读着读着就会发现,除了思想的清晰和犀利以外,他的“平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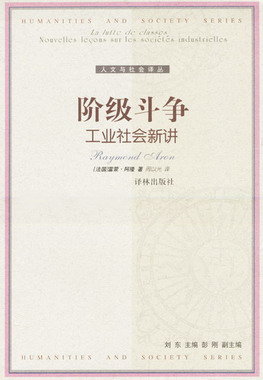 无奇”中还蕴含着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我们这里不太熟悉但却引人入胜的精神气质。我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就时常产生一种冲动,很想像哈姆莱特对那个鬼魂一样地大喊一声:“哈!你这个老田鼠!”
无奇”中还蕴含着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我们这里不太熟悉但却引人入胜的精神气质。我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就时常产生一种冲动,很想像哈姆莱特对那个鬼魂一样地大喊一声:“哈!你这个老田鼠!”
当然,雷蒙・阿隆会对我这一声喊很不以为然的。他最警惕的就是这种审美化、抒情化的表达。他的精神气质要概括起来表达也很“平淡无奇”,只两个字:“审慎”。他是一位学者,一生著述甚丰,又是一位政治评论家,凡遇公共生活中的大事都会表明态度,发表言论。他的回忆录副题叫做“五十年的政治反思”,几乎是语不及个人生活,整个回忆的就是自己五十年间针对法国、欧洲和全世界发生的政治事件的著述与言论。从中可以看出,他一生的著述和言论都是审慎之作,而回忆录本身也写得很审慎。这种审慎并非仅仅表现在言必有据上(那是最起码的要求!)。更重要的表现是,他总是有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主张,随时准备着受人质疑、与人讨论。用他的话说就是:“永远不要急于下定论,也不要以绝对真理已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论敌。”
 这样一种审慎的内涵当然远不止是性格谦和、说话小心,而是自觉养成的一种在智性上的有所节制,其根基则是对人性、社会和历史的某种清醒而透彻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是雷蒙・阿隆个人饱学深思的结果,而且也渊源有自,植根于西方思想的自由主义传统之中。
这样一种审慎的内涵当然远不止是性格谦和、说话小心,而是自觉养成的一种在智性上的有所节制,其根基则是对人性、社会和历史的某种清醒而透彻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是雷蒙・阿隆个人饱学深思的结果,而且也渊源有自,植根于西方思想的自由主义传统之中。
2
如雷蒙・阿隆的好友、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指出的那样,阿隆“既致力于追求启蒙运动的理想,但又有所保留”。启蒙运动的理想是一种基于理性力量的信仰,追求这种理想在近世欧洲知识分子中可谓极为普遍,并不特别。阿隆值得一说的是“有所保留”。之所以“有所保留”,是因为认识到人类的理性毕竟是有限的,而理性的力量既无可能也不应该把非理性的习俗、传统等等力量从人类社会中驱逐尽净。借罗杰・金巴斯评论的话来说:“如果就启蒙运动信奉世俗主义、人道主义、理性对迷信的胜利这些观念而言,可以称阿隆是启蒙运动忠诚的儿子。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称他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着力批判的那个旧式传统社会的忠诚的‘孙子’。当启蒙思想批判一切信仰,只承认自身这种基于理性力量的信仰时,就趋于成为一种浅薄的思想了。”
 事实上,阿隆的“保留”不仅仅是因为意识到这种“浅薄”,更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这种“浅薄”会引出极端荒谬的结论。简言之,只信奉理性的力量,会带来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一方面是相信理性有力量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并最终能让人类控制和操纵自己的历史(控制和操纵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另一方面是认为人类应该彻底地与非理性的过去决裂,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创造历史。基于这种乐观主义,某些“缺乏耐心的理性主义者”就会把暴力视为“最后的手段”,时常受到暴力的诱惑(阿隆因此有言:“暴力本身的吸引力、诱惑力要大于排斥力”!),并因此容忍甚或支持极权政治。而这一切,已经为20世纪的历史所证实。
事实上,阿隆的“保留”不仅仅是因为意识到这种“浅薄”,更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这种“浅薄”会引出极端荒谬的结论。简言之,只信奉理性的力量,会带来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一方面是相信理性有力量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并最终能让人类控制和操纵自己的历史(控制和操纵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另一方面是认为人类应该彻底地与非理性的过去决裂,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创造历史。基于这种乐观主义,某些“缺乏耐心的理性主义者”就会把暴力视为“最后的手段”,时常受到暴力的诱惑(阿隆因此有言:“暴力本身的吸引力、诱惑力要大于排斥力”!),并因此容忍甚或支持极权政治。而这一切,已经为20世纪的历史所证实。
作为“自由派”的阿隆则持有一种“悲观主义”,他说:“自由派认为人始终是不完善的,并听任这样一种制度存在,即‘善’将是无数行动的结果,而永远不是一种有意选择的目标。在此范围内,它赞同悲观主义,即将政治看作是一种创造条件以使人的缺陷有助于国家的善的艺术。”所以阿隆又强调说:“权力的分散是自由的条件。”在“自由派”看来,能在社会生活中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也即能将个人受制于他人的专断意志而产生的专制状态及其恶果降低到最小限度),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善”。对于那种认为“自由本身不是目的,只有联系伟大的目标才有意义”的论调,阿隆引用托克维尔的名言回答说:“谁要从自由之中寻求自由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侍侯人。”
除了秉承自由主义的传统以外,还有一种对立的力量使得阿隆更加警觉地谨守着“审慎”原则,那就是:他的“左派”论敌们因“在智性上无所节制”而信口开河发表的某些言论。举个小例子说,萨特在1954年访苏归来后说:“在苏联,人们拥有全面的批评的自由。”以萨特卓越的智力,做出这种完全与事实不符的判断是令人惊讶的。你只能认为他因“耽迷于意识形态的妄想”而成了睁眼瞎,看不见事实了。阿隆说:“那些只乞灵于观念而对事实不予尊重的人,时而以观念的名义驳斥事实,时而又用观念的名义为事实辩护。”于是,从观念出发推论出“事实”,取代了从经验出发对事实做出判断。
在这里要评述阿隆与萨特几十年的争论显然是不合适的。扣紧我们的主题,指出萨特不具备“审慎”的气质则不会有什么不妥。萨特曾说阿隆“对于胡说八道过于战战兢兢”,而阿隆则反击说:“萨特在政治上却常常滥用犯错误的权利。”阿隆还曾评论道,萨特之所以“不赞成平凡的社会改良,而成为口头上的激进革命论者,只是出于一种伦理激进主义,加上对社会结构的无知,以及对资产阶级情绪上的憎恨”。根据阿隆诸如此类的评论以及萨特的某些言论和著作,我推测,萨特其人偏爱观念、崇尚激情、赞美充满诗意的生存,在气质上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平淡无奇”。所以,“审慎”的气质在他眼里也许与资产阶级的市侩气也相差无几。当然,这只是推测。
3
回过头来再谈谈我们这里的1980年代。如果我的上述推测不是太离谱,那么萨特在1980年代的风靡一时和阿隆的姗姗来迟就都不完全是偶然的了。前一阵许多人在回忆“八十年代”,大都说起那是一个浪漫的年代。渴求“思想解放”和张扬自我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那时候哪来得及理会“审慎”二字?相反,萨特高调论说的“自由”却是恰逢其时。依我之见,萨特当时最能打动我们的思想,是否弃了历史总体性和历史必然性,而强调个人选择(每个个人冒着风险投入历史进行选择)的决定性(或本体论)意义。这样一种自由观,表达起来还常常具有一种审美效应,对于文化人尤具吸引力:注定孤独的人,总是背负着无限的自由的重压,不得不(或有“责任”)做出选择云云。相比之下,“自由派”阿隆所坚定维护的“自由”(简言之即“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当然又显得”平淡无奇”。我们这里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一不小心就用审美取代了理性思索原也是一种积习,“八十年代”似乎此风尤盛。也难怪,“饥荒”之后嘛,吃一口夹生饭也觉是美食。当年我曾稍有夸张地表述过我所观察到的此类现象。――谈到海德格尔,就听见有人赞叹:“此在,啧啧!”仿佛“此在”这个概念就是一道美味佳肴。
读阿隆让我明白,这种现象是世界性的,在我们这里也不会随着“八十年代”的逝去而消失。阿隆告诉我们,厌烦“平淡无奇”(尤其是商业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平庸乏味”)、偏重审美效果和迷醉于观念而不顾事实,是知识分子容易染上的一种痼疾。由此产生的浪漫情怀和激进思想,其实常常包含了某种怀旧情绪。在我看来,他对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追问,在我们这里同样令人警醒:“但是为什么知识分子自己不承认他们感兴趣的是其作品和生活的精致考究,而不是工人的生活水平呢?为什么他们事实上是竭力为贵族制的价值观辩护,以使它们免受大众商品和普通民众的侵蚀时,却要极力抱住民主制的各种行话和术语不放呢?”
已经过了一个“九十年代”,眼看着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又要过去,但愿这一回我们不要错过总是想把“意识形态的诗篇引向现实的散文”的雷蒙・阿隆,并且能牢牢记住他奉为圭臬的伯克的名言:“审慎是这个俗世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