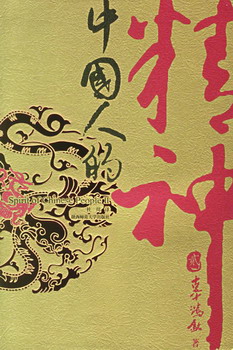
精神》(中)、《中国人的精神(贰)》(右)
近日,笔者在书店看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推出的《中国人的精神(贰)》一书,先是甚感迷惑,因为从来不曾得知辜鸿铭还有过又一部以《中国人的精神》为名的著作。开卷方知,这部所谓《中国人的精神(贰)》,其实不过是将辜氏《尊王篇》和《清流传》两部译著进行的“再包装”而已。如此这般忽悠读者的拙劣手法,已让人感到相当不快。待阅其编排和内容,见其粗制滥造,且对筚路蓝缕的先驱译者竟采取“故作不知,掩耳盗铃”的无赖损招,更是平添恶感。于是将书买下,连同去年所购由同一出版社所出的《中国人的精神》中英文对照本,一并加以审核。
笔者之所以购买此两书,因为家中藏有1996年黄兴涛和宋小庆翻译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首译本和2001年的重印本,另存有黄兴涛主持翻译的厚重的两卷本《辜鸿铭文集》(均为海南出版社出版)。两相对读之下,不禁感慨四端:既为抄袭者“耻”,复为原译者“愤”,更为出版社“怜”和出版业“叹”。关于《中国人的精神》
先来看看署名“陈高华译”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该书出版于2005年10月。但凡是较难一点的诗歌翻译,尤其是拉丁、法文和德文的诗歌,都一律照抄黄兴涛的译本,且一字不漏。其他的地方也可看出是在黄兴涛等人的译本基础上直接进行“来料加工”,其在文字上略施花招,不仅多属无谓,反而破坏了原译的严整和流畅。尤其可叹的是,这位“译者”毫无中国近代历史常识,为了在一些人名翻译上造成不同于黄译的假象,直如吃错药一般,故意把一些通行的固定译名改得面目全非。例如,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杀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生硬地改译为“科特勒”,著名法国汉学家儒莲被改为“于连”,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大臣毛奇莫名其妙地被改译为“威尔海姆”和“莫尔特克”,甚至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都改译成“陈尤金”,清末的“外务部尚书”则被改为“外务部长”,“海关总税务司”被改为“海关检查长”,等等,不一而足(可参见该书第8、13、17、24、204页)。而且这种改动前后还并不统一,甚至一篇之中也是混乱不堪,如附录“群盲崇拜教或战争与战争的出路”中反复出现的热爱中国文化的剑桥大学教授迪金逊(Lowes Dickinson),这位新“译者”译作“狄金森”原也未尝不可,但这篇附录中却忽而“狄金森”,忽而又“迪克逊”,完全是随意乱用(参见226、232、233、239等页)。前文提及的法国汉学家儒莲在正文中被改为“于连”,而后面所附的注释却仍然是“儒莲”;英国历史名家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被故意改为“佛禄德”,而后面的注释部分竟然又回到“弗劳德”!凡此种种,实在不能不让读者怀疑,此译编很可能不是一人所为,而是多人胡乱东抄西凑而成的“伪劣品”。
说到译著后面的注释,就更不能不为原译者生“愤”了。黄兴涛等人的译本包含了很多精心的注释,尤其是那些考证性的注释,如理雅各弄错了《皇清经解》完成的时间,翟理斯《古今姓氏族谱》一书的内容介绍,以及那些古文词句的对译之类,都是真正的专家功夫。没想到这些在专业圈子里都难能可贵的注释,如今竟被人要么全盘照抄,要么随意胡乱删减,不仅从不注明来源,且抄错的地方比比皆是。如影响辜鸿铭很深的马修・阿诺德,黄兴涛等原译者曾在注释中介绍说“他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十分厌恶”,新“译者”所做的注释却是“[他]批评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厌恶”(该书254页),令人啼笑皆非。另有的地方,在黄氏原译本中属于未能校出的古文排印错误,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厚”字被误写成了“属”字,这位“陈高华”竟然也亦步亦趋,错得毫无差别(该书第111页)。这如果不是盲目抄袭,谁能有更好的解释?关于《中国人的精神(贰)》
其实,事情倘若仅限于此,笔者可能还懒得搭理。但这时又见到了《中国人的精神(贰)》,发现其抄袭之行径更为放肆,实在已无法容忍而不发一言。笔者相信,任何一个喜爱辜鸿铭和珍惜干净学术环境的读书人,对此种行径若再姑息迁就,不起而揭露,则自己的良心都不免觉得难安。
《中国人的精神(贰)》标明出版时间为2006年10月,署名为“杜川译”。此“杜川”连前此那般作“穿插改字”般掩人耳目之举的耐心也全部失却,许多部分干脆就整章整节、完完全全照抄黄兴涛等人所译《辜鸿铭文集》(上)。据粗略估计,《中国人的精神(贰)》全书22万字,大约90%甚至以上,都直接抄自《辜鸿铭文集》中的《尊王篇》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即《清流传》)两部分。
以《清流传》为例,其“卷首引语”、“再版记言”、“导论”、第三章“满州贵族重新掌权”的第三段以后文字,第四章“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尾声”,以及附录“已故皇太后”和“中国皇太后”等,都是全盘照搬黄译,很多地方甚至一字未改,如《中国的皇太后:一个公正的评价》等部分。《已故皇太后》一文仅改了四个字(一是在标题“已故皇太后”前加了“关于”两字,一是在开头的称呼“先生”前加上了“编辑”两字)。“尾声”部分仅改两字(也就是将“末了”二字改为“最后”),第四章也仅有个别文字的改动(如把“文人学士”改为“儒生”等)。《尊王篇》中的情形大致相同,如“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的“之三”到“之五”及“跋”,附录“文明与无政府状态”和“美国海军将军艾文斯致辜鸿铭的信”等,均属全盘、完整地抄袭黄译。
该两书中其他篇章节目中,或大或小、间隔抄袭的段落也举不胜举。即使有些改动的部分,也大多是在黄译的基础上,采取以下三类变相抄袭伎俩而成。其一是改“马铃薯”为“土豆”、“大英帝国”为“不列颠帝国”、“东西”为“玩意儿”之属;其二是隔几行故意添几字之属(如句前加“依我看”,或“某地正在出售人肉”被无端改为“某地一些城市的菜市场上正在出售人肉”(见《中国人的精神(贰)》,第103页),或“端王的儿子”之后被莫名其妙地加上“爱新觉罗・溥傀”);第三是前后故意颠倒顺序之属。特别是最后一类,对译文的语气和顺畅性影响最坏。
此两书最后的注释部分约2万余字,除两个小注外,也都抄自黄译,且大都一字不改。此外,其中有关“比肯斯菲尔德”的注释还彼此重复矛盾。而黄氏译本中原有的一些重要注释,如《清流传》第二章最后一个反映辜鸿铭宪政思想的千字长注,竟被新“译者”全部删掉。
黄兴涛等人所译的《尊王篇》和《清流传》中,一共有长短不一的三十首诗。这些诗翻译起来十分不易,而黄译总的说来译得相当漂亮。对这些译诗,“杜川”在《中国人的精神(贰)》中也一首不落、一字未易地加以了“吸收”。实际上,笔者最初怀疑“杜川”抄袭,就是《尊王篇》篇头那首长长的,占两页篇幅的《怀念赫尔曼・布德勒(已故德国驻广州领事)》一诗引起的(可将该书第1-3页此诗与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第3-6页此诗相对照)。正是这首既优美又富有哲理、令人沉思的诗歌,以及《清流传》中那些幽默而谐趣的译诗,才使我在似曾相识之余,顿时想起了《辜鸿铭文集》。
在对勘译本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中国人的精神(贰)》的“译者”甚至可能连辜氏的英文原作也从未见过,而只是将《辜鸿铭文集》中的有关内容扫描以后,加以简单处理而成。这从黄兴涛等人译本中的几首诗歌被新“译本”混为一般文字,甚至黄译对《尊王篇》和《清流传》等的介绍部分也被新“译本”混为正文等表现中,可以推见一斑。
当然,黄译本身并非完美无缺。仅就校对而言,其笔误和舛错之处也是有的。如《尊王篇》的“近期札记之五”中辜氏将“义和团”民比作法国的“无套裤汉”,在《辜鸿铭文集》中就被粗心地误作“长套裤汉”;《清流传》第三章认为英国人不应当讲中国人“如魔鬼般无情之类混话”,其中“混话”二字也被误写成了“混活”,等等。奇怪的是,这类极为明显的简单错误,休说只要稍微看看英文原文,哪怕只要略微耐心地对读黄译上下文,本来都完全可以加以矫正,而“杜川”先生竟然也毫不觉察,一并继承下来(见《中国人的精神(贰)》,第114、199页)。由此可见,说《中国人的精神(贰)》抄袭《辜鸿铭文集》可能还未必十分到位,对其中许多部分,更为恰当的说法,或许应该是“复制”或“扫描”后的“粗劣加工”。
在对读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贰)》时,笔者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凡“陈高华”改过的黄译人名,“杜川”却都又一律还原为黄氏译法,虽前后矛盾如此,而责任编辑却为同一人。
笔者曾经善意地想象,这两本所谓新译的出现,可能纯属非法书商的盗窃行为,与陕西师大出版社无关。但当我通过朋友直接咨询该社领导的时候,他们却明确地说,这两书不仅是他们出版社所出,而且是“重头”成果,并且让我拿出抄袭的证据来――这曾让我先是气恼,后是悲哀了好一阵。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证据――也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强烈抗议。我想我应当建议被公然抄袭的译者,对此种恶行毫不犹豫地诉诸法律。同时,我也真切感到,译著版权究竟如何才能切实地进行保护的问题,确实也已到了不能不引起国内出版界和法律界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