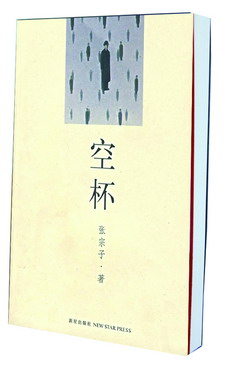 继《垂钓于时间之河》,张宗子的第二部散文集《空杯》日前已出版。笔者有幸得以先睹,正如所预期的,一口气将手稿读完,感觉回味悠长,十分享受。这部文集内容和形式都很丰富,而且自成对比,互相轩邈。有叙
继《垂钓于时间之河》,张宗子的第二部散文集《空杯》日前已出版。笔者有幸得以先睹,正如所预期的,一口气将手稿读完,感觉回味悠长,十分享受。这部文集内容和形式都很丰富,而且自成对比,互相轩邈。有叙
一、“师承”
宗子的文字,不事藻饰,不作奇语。这种风格的散文,好处在于它的闲适、恬淡;它并不拘泥于义理、章法而古板呆滞,更非顶着一股纱帽之气。它好似一位情投意合的朋友,和你促膝共语,海阔天空无不随意谈来,间或有妙语闪现,得于言而会于心,如此而已。
钱锺书说魏晋散文在骈体之外另有种不衫不履的“家常体”。“不骈不散,亦骈亦散,不文不白,亦文亦白,不为声律对偶所拘,亦不有意求摆脱声律对偶,一种最自在,最萧闲的文体。”这种萧闲自在的风格,产生于魏晋,不亦宜乎!这是与庙堂文字抗礼的另一种格调,飘散于历代的尺牍笔记中,一路延绵不绝,到苏黄,到明清小品随笔,到鲁迅的散文。现在不是已经有了宏大富丽的大散文吗?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宗子的散文属于另外一格,是“小散文”,是那种纯粹写给个人、不预设听众的文字,是那种在家里跣足敞怀、穿大布犊鼻?的文字――不信还请读读他所作的大量读书札记、断想、随笔。
为文的风格是性情的反射。宗子师法魏晋,那种通脱不羁的气质,也在他的文章中氤氲。宗子的文字虽然谈的是平常人之事,气质上却略带“仙”风;难怪他非常欣赏魏晋的神异故事,认为其纯粹乃是后世再难一见的。其实它的源头就是庄子。我未见庄子烂熟于胸如宗子者,其纵横恣肆,“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的神韵,与他的天性极能契合。尽管他的文字在风格上并没有太多庄子的影子,但是那种无拘无束、自适其适的精神仍在,它潜藏在文字的底层,以比较温雅的方式透露出来――我以为自在的精神正是一切好散文所必需的。宗子说,“读庄子,你可以说气,可以说神,可以说意,唯独没有章法”。他的性情自然是不喜欢束缚的,每每乐道于梁简文帝萧纲诫子之语:“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在外国作家中,博尔赫斯、普鲁斯特、波德莱尔都是能摆脱思想、文体的束缚的,他们对宗子的影响比较深,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宗子毕竟是宅心温厚,少了波氏那种viciousness(恶意);也许宗子的文章中多一点刻薄和讥诮,当能另添一番风味。
二、学养
宗子的散文得益于厚实的修养,因而读来饶富趣味──我一直以为好文学必是有味道的文学。他讲蚊子,劈首就是鲁迅的好句:“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蚊子吸血,原来还吸出了风格:广州的蚊子可谓布道家,下嘴之前必有一番聒噪的演说,嗦嗦,惹人厌烦;厦门的蚊子就不同,上来就是一口,干脆利索,倒也算是豪杰的勾当。有一种“猛捷如花鹰”的豹脚蚊,古代典籍提到最多,就是花脚蚊子而已,宗子见它体态优雅轻盈,花色也素淡富有节律,居然想到了健身的女人和时装设计,要向他们郑重推荐呢。
宗子吃石榴,也吃得饶有趣味。他喜欢石榴,是因为喜欢石榴花,连带喜欢石榴花的诗词,又读到瓦雷里的诗,说石榴是智慧的象征。于是发愿一定要找到一颗完美的石榴,没有一个籽儿受伤,然后细细剥来,一个籽儿也不弄破皮,而这“也许比得了几本好书,看了一场好电影,中一次刮刮乐彩票小奖还要高兴哩”。何以如此?只因石榴籽太娇嫩了,嫩得只好侵占形容女人皮肤的词儿;可是若能完整地剥了下来,放在细瓷小碟中,精美不可方物,在理想主义者眼里,这是极至之美的境界。可惜这样“真理”般完美的石榴,却一直没有出现;过了那么多道人手,哪能个个都存怜香惜玉之心呢?这里已不是在说石榴了,说的其实就是智慧:完美的智慧,即是这般难得。
宗子的散文、札记、随笔,游弋于广袤的古典文学传统之中。有如鱼与水的关系,水绝对不是鱼的桎梏,相反,它不但提供了养分,更给了鱼施展的天地。宗子说:“传统是无限的自由。”这个看法是很值得玩味的。传统,自然并不限于中国的古典,也包含西方的,广言之,是人类文明全部的积累。若能浮槎畅游于其间,到了那种境界,该是何等的幸福!
三、语言
读张宗子的文章,还有一项享受,就是欣赏他的语言之美。他的文字,读来宛转流丽,音调铿锵,既有白话的亲切自然,又带文言的雅正端庄,是难得一见的好文字。比如,他写吃辣椒,感慨:“喜欢酒而不善饮,喜欢茶而不精其艺,喜欢古货而不能常得,喜欢辣而徘徊止步于登堂入室之前,我只能超出象外,舍实求虚,会其意而已矣。人世有如此多的事物让人喜欢,让人陶醉,让人梦绕魂牵,这正是上天对人恩厚的地方。一念及此,我是幸福的。”
张宗子的文章读来都具有很强的音乐感。其实老辈的文人,都十分注意这一点,比如在一则广为流传的轶事里,西南联大研究庄子的刘文典,就曾说过好文章不外“观世音菩萨”几个字。其中“音”就是文字的音韵。汉语是世界上最具音乐性的文字,文学作品可诵可吟,不充分展示这个优势是没有道理的。宗子曾讲起他作文的诀窍,说每写完一篇文章,一定要诵读一番,看音韵的流动是否顺畅,有抑扬之感,有时这里添补几个字,那里删去几个字,有时觉得一句话好像只有一条腿,立不起来,于是少不得补上半句、几个音节以平衡文气,虽然于意思上可能并没有多大作用。我觉得这话说得十分中肯。宗子浸淫于古典诗词歌赋,那种音韵之美便逐渐深入到骨子里去了,一下笔就能表现出来,成了作者风格的一部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汉语的写作竟开始衰退了;我们看到,整个20世纪,其实并没有多少像样的诗歌、小说、散文,我们读的、记诵的还是几百年、上千年前的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为汉语的命运忧虑。然而宗子仍然是乐观的,他在诗中说:“汉祚中原不可移。”对博奥的汉语深具信心。他的话值得一引再引:“世界上很少有一种语言,像汉语这么优美、精雅、丰富、细腻、深刻,而且强大有力。它的画面感,它的音乐性,它的柔软易塑,它的准确犀利,让我只有庆幸。这是经过无数天才熔铸过的语言,是从庄子、列子、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三曹、嵇阮、庾信、李白、王维、杜甫、韩愈、苏黄和周邦彦、姜夔手里出来的语言,是唐诗、宋词和元杂剧(特别是《西厢记》)的语言,是《红楼梦》的语言。”于是我们现在读宗子的文字,便有了一层更深的现实意义了。 《空杯》,新星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23.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