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被激进的政权破坏殆尽,然而处在国土边缘的人们却并没有忘记他们的根,他们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诉真道,想尽方法来传承自己民族的记忆。但是真正注意这种努力的,除了无处不在的密探,就是来自外星的观察员。但更为讽刺的是,这名观察员萨蒂,故事的主角,恰恰就是一
这样一个已经被自己的深层经验笼罩在恐惧之中的观察者,如何能摆脱阴影,公正不倚地看待这个星球上的变故?当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位置交换,个人又该如何完成认知上的升华?这些问题都蕴涵了深刻内涵。但作者厄修拉・勒奎恩可不想把脚步停在这里,在我这样的读者看来,她似乎更想说的是:
文化记忆为何要在人们的心灵中顽固留守?
人们确实有一种美化过去的冲动,在回忆中,我们会不自觉地把从前镀上一层金色,认为淳朴都存在于旧日,而道德都败坏在今天。因为这种想法,试图留住以往,成为了人们的本能。但消亡永远是真理,每时每刻,都会有无数的东西走向绝迹,对人类来说,说每一天都是终结之日也不为过。但是我们真的失去这些属于过去的东西了吗?实际上,在对历史的回顾中,我们能够把握自己的文化之根,可以说,文化就是一种感觉――体会到什么是“我的东西”、“我的意识”、“我的自觉”。
萨蒂在作为观察员的开始,最感困惑的,是她无法窥测到这个星球上的“我”。运转良好高效的政府展现的是完美的一面。人们用一种声音说话,这是一种“非我”的状态――你虽然能听见对方在说话,虽然他说的无比正确,可是你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也由此,寻找“我”在哪里,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萨蒂的任务。在这个任务的执行过程中,萨蒂时时刻刻地在回忆,她过去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并没有因为自己超然物外的观察员身份而淡化,反而因为孤独,变得格外鲜明。
同样又是个讽刺的设定,在富饶和先进的城市已经空虚到没有任何意义留存时,乡村却成为了文化记忆坚守的最后领地。显然,号召人们返回乡土已经是过时的行为了,“寻根”不应该是对陈旧的生产方式的眷恋,小国寡民,只是听上去很美,人们的生活不可能倒退,时间在滚滚向前,我们所能做的,唯有倾诉。
倾诉,telling,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词语。在故事中,我们看到,负责向其他人传播经验和知识的长者,都被尊称为梅茨,他们的责任就是把几近消亡的旧文字中的思想传达给那些不识字的人。由“我”告诉“你”,“对于神圣的仓促一瞥,不用你相信,只需你聆听”。这种完全经验化的传递方式,正是被外来传入的“先进文明”所诟病的地方:你说的是真的吗?可以再现吗?没有亲眼见过的事情,我们不会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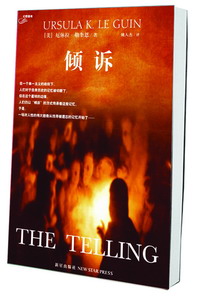 我们只会相信那些被科学和实验证明了的东西,所以督察官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只会相信那些被科学和实验证明了的东西,所以督察官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永远不想再回到蛮荒的时代。”
没有唯一正确,这是“科学”所无法忍受的;仅仅是模糊的“好”,这种形容词无法让“科学”满足。“科学”让“正确”代替了“好”,“好”有很多种可能,而“正确”却只有一个。
文化记忆到现在已经成为了“文明”的绊脚石,人们试图像从前那样宽容,却被告知,你们必须选择一方,非黑即白,没有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截然两分的艰难抉择中,古老的传统再次败退,但是她依然不屈不挠地选择了委曲求全――如果你们不容许我,我就寻找新的藏身之所;如果你们烧光我的书籍,我就躲进人的心里。
没有文字,我还有语言;没有语言,我还可以舞蹈。
传说与故事在铲车的面前固然不堪一击,但是文化的魂魄却能盘旋在人们的心中千百万年。我们不能通过他人的生活方式来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只能在自身的历史中看清身份与血缘。这种意识深深植根在我们的灵魂之中,让我们能够自豪地与他人区别,使我们不畏惧于迷失方向。哪怕到了万物凋零殆尽之际,我们也能够清晰地分辨自己的身份,这,就是《倾诉》所要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
《倾诉》,[美]厄休拉・勒奎恩著,姚人杰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