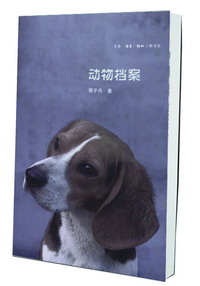 当你想行善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可怕的无能为力,不能如你所愿地帮助其他生命。接着你就听到了诱惑者的声音:你为什么自寻烦恼?这无济于事。……你能
当你想行善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可怕的无能为力,不能如你所愿地帮助其他生命。接着你就听到了诱惑者的声音:你为什么自寻烦恼?这无济于事。……你能
做的一切,从应该做的角度来看,始终是沧海一粟。但对你来说,这是能赋予你生命以意义的唯一途径。……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减缓了人或其他生命的痛苦和畏惧,那么你能做的即使很少,也是很多。保存生命,这是唯一的幸福。
田金平和张诗媛的经历基本相似。早先都是国营大厂的职工,因工厂改制或倒闭而下岗,做起了小买卖,一个开鲜花店,一个开彩色胶卷扩印点,虽然赚钱并不易,可也都有了些积蓄,小日子过得很有起色。她们原本平静的生活,似乎都在1995年发生了转折。这一年《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出台,街上被人遗弃的小狗多了起来。出于对小动物的同情,她们在完全不知深浅的情况下,开始了自发的救助。差不多十年过去,她们的生活由小康下降到贫民水准,城里的住房出租给别人,微薄的房租加上退休金,再加上断断续续的社会援助,根本不能支撑日常的开销。没有休假,没有社交,除了必要的采购和带动物看病,她们长年寄居在陌生封闭的环境里,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一台付费不菲的电话。对于这一切,当初她们显然估计不足。
田金平在村口的路上迎接我们,头发乱蓬蓬的,坐到车里,就带进来一股刺鼻的气味。田金平的院子里到处是乱跑乱叫的狗,大约是看到新的面孔,小狗全都兴奋起来,有几只还齐刷刷站起来,直往我们身上扑。田金平把我们让到屋里,但屋里也几乎无处落脚。就在见面寒暄的功夫,一只狗已经趁人不注意,在田金平卷起来的铺盖上结结实实撒了一泡尿,那儿正是她打算让我们入座的地方。我环视这间十来平方米的屋子,乱七八糟就像刚被什么人抄过家似的,除了五斗柜上一个插着几枝仿真花的花瓶,还可以看到主人当年安适的生活印迹,真有些满目疮痍的感觉。
正在说话,张诗媛抱着一只小狗来了。她住在离这儿十多公里的另一个村庄,今天出来主要是为了给患了眼疾的八哥犬打封闭,听说李教授要过来,顺便也见见面。我们借用田金平房东家的厢房谈话,带来的干粮是宾主共进的午餐。几个普通的芝麻烧饼,让她们吃得香极了,时不时还要喂一些给各自抱着的病狗,喂干粮的时候,她们会掰下一块在自己嘴里嚼嚼,再塞进小狗嘴里,吃上几口之后,还让它们在自己的水杯里喝水。如此你来我往,自然得就像一个喂食婴儿的母亲,完全没有障碍和界限。
回头整理录音的时候,我发现这一卷磁带的声音嘈杂得几乎听不清楚。一来是两只小狗因为伤痛不停地叫,二来是田金平和张诗媛都在抢着说话,反复听了多遍才算理出了头绪。
关于她们收养小动物的起因
田金平说,我的店正好紧挨着一家宠物店,有些弃养小狗的主人常把病狗扔在门边,宠物商怕自己的正要出售的小狗被传染,赶它们走,打得滋哇乱叫,我看着不忍就收养下来,一只两只十只八只,直到现在的三十多只狗、四十多只猫。
张诗媛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也算有点钱了,到市公安局的动物收容所去赎没收的小狗,一次就交了罚款差不多一万块钱。从来没想过,这条船一旦你上来了,就只能往前划,钱像是扔在水里,响声也没听见一声,更糟的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岸在何方。
关于她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张诗媛说,有几年没吃过像样的饭了,好不容易包一顿饺子,一只狗就去掉二十多个,再喂一轮,自己就甭想吃了。现在我们头发都白了,买瓶染发剂只敢买六块钱一瓶的,别人说这种伪劣产品染了要得癌症,那也没办法。
田金平说,我一天做一顿饭,多半是粥和面条,哪怕泡个方便面,小狗闻到香味也围着你,盯住你的嘴,叫你没法往下咽。为了维持开销,我连易拉罐都捡过。赞助也有一些,但经常没有保证,不到万不得已,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老找人家热心的人开口。
关于她们各自的家庭和朋友
田金平说,我当时家庭有些不和,是小狗们安慰了我的情感,成了我的第一需要。我跟丈夫分手之后,儿子摔伤了我都没法照顾他,现在他也不爱理我了,就连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也因为我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再跟我来往。要是说朋友,干我们这行的没有真正的朋友。当初也是几个朋友说,咱们一块儿来干,你在这儿管着狗,别的事情大伙帮你张罗。刚开始还行,现在时间长了,也没人过问了。我已经好几年都是孤零零一个人过年了,就是一个人守着这几十只狗和猫。不瞒你说,志愿者送来喂狗的鸭架子(烤鸭店片过皮剥了肉的鸭骨头,常被卖出来当狗食)做过我的年夜饭。
张诗媛说,我和我丈夫本来已经要分手了,是因为这些小狗才挽回了我们的婚姻。我丈夫也爱狗,救助流浪狗他也没二话,有时候,给受伤的狗治伤,屎尿澎了一脸他都不怕脏。我寻思他对狗都这么好,从根儿上说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也就不再提离不离的事了。现在我们远离城市和人群,有他相助我怎么着也比她(田金平)好多了。至于朋友,甭想有什么朋友。守着这一大群活口,你出去吃顿饭都没心思,惦记着速去速回,根本没有跟人扎堆儿的条件,就得忍受孤独。谁叫你干这个来的?
关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张诗媛说,谁都说我们是走火入魔的一伙人,是狗痴。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我就是爱狗,爱狗胜过爱人。狗从来知恩图报,人呢,不恩将仇报就挺够意思了。在我眼里,狗就是艺术品,人就是渣滓。谁不爱狗我就恨谁,鲁迅嚷着要痛打落水狗,我连他也一块儿恨。
田金平说,不少人说,救助珍稀野生动物还有点儿意义,弄这么一堆破烂狗养着,叫什么事业?说我们都是精神病。这种压力比经济困难对我们的考验还要大。有时候,我都快受不了了,但一看见小狗们饿着肚子求救的眼神,我就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扔下它们不管。其实我们都是无名小辈,人们骂得最多的是芦荻,她是名人,还不也背着精神病的名声吗?
关于是否对自己的选择后悔
田金平说,不能说后悔,但还是怀念过去的时光。我最喜欢旅游,早些年就青海西藏新疆都去过了,多好玩呀!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回到那样的生活里去了。
张诗媛说,要说一点儿不后悔也不真实,当时谁知道这事开了个头儿就没有尾。人家知道你捡狗,就不断扔给你,我们早就说,不能再领了,但一看到小狗受苦受难,就忍不住又领了。看自己救的小狗们无忧无虑玩耍的样子,又把什么都忘了,理智一点儿作用都没有了。
关于前途和希望所在
田金平说,我们不知道前途会怎么样。我们一边捡人家一边扔,别说捡不过来,就是都捡回来你也挡不住狗还在不断地生,总有一天会弄到满街都是流浪狗和猫,那是多可怕的事儿。中国是到了人口爆炸的时代才开始计划生育,现在猫狗不绝育也会大爆炸。我们的想法没人理会,政府也不管。我们希望政府早点儿出台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对养狗的人有约束。乱拉大小便,狗叫声扰邻,有问题应该处罚人,不能处罚狗。狗懂什么,它们没有能力做出选择。
张诗媛说,以前我连市长是谁都不知道,救助小动物之后,也关心起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来了。媒体和政府都得转变观念,别什么事都光拿经济价值来衡量。我们现在苦撑苦熬的,就是在等待政府出台相关的法律,让小动物有安全保障,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我和我老公打算这辈子要把已经收养的这二十多只狗都送了终,但我们不会让儿子再做这些事儿了。
从田金平的小院出来,我们还要到张诗媛家里去看看。分手的时候,田金平留下了我的电话,说还有许多话想说。看着她零乱的着装,看着她无助的神情,我心里涌出的是一种绝望的怜惜。
让我们完全没料到的是,张诗媛亲自带车去她自己家,竟然差一点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按她的指点左拐右拐,不断用手机联络她丈夫,才在跑了几十公里冤枉路之后,到达了目的地。对此,张诗媛解释说,我只认得家门口的公共汽车站,而且只要出门一定抱着生病的狗。上了车,心里光顾惦记别让售票员给撵下去,没有心情看风景,所以也不认得路。
汽车的雨刷在玻璃上刮来刮去,使我们原本已很沉重的心情更添了烦闷。仨瓜俩枣的捐助,三言两语的交谈,对陷入了这个永无止境的泥沼中的人们,能有多少帮助呢?我和李小溪都沉默着,回城的路因此变得更加漫长。想着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女人,想着所有与她们的经历相近似的女人们,我的心里就像灌了铅一样,沉甸甸地钝痛。
几乎无一例外,她们用善行将自己置于绝境,究竟该如何理解和评价她们,难道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或许我们压根就无法也无须对她们做出心理的、常识的分析。
一九五二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贝特・施韦泽在《斯特拉斯堡布道》一文中这样阐述人的行善:
当你想行善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可怕的无能为力,不能如你所愿地帮助其他生命。接着你就听到了诱惑者的声音:你为什么自寻烦恼?这无济于事。……你能做的一切,从应该做的角度来看,始终是沧海一粟。但对你来说,这是能赋予你生命以意义的唯一途径。……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减缓了人或其他生命的痛苦和畏惧,那么你能做的即使很少,也是很多。保存生命,这是唯一的幸福。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这段文字抄录在这里,是想给因行善而处于绝境的人们找一点儿精神上的支撑吗?其实在我的内心,真的不想鼓励她们在暗无天日的迷途中继续前行。而且,相对于她们无底的困境,这些话显得这么抽象、这么轻。
时至今日,我听说她们还在绝境中孤独守望,等待着她们想象中效力显著的动物保护法出台的那天。这几乎是她们唯一的精神寄托所在。
(本文摘自《动物档案》,蒋子丹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月第一版,定价:3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