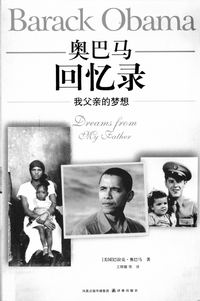 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当时我住在纽约哈莱姆以东和曼哈顿区交界处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九十四街,那里的环境并不怡人,草木贫瘠
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当时我住在纽约哈莱姆以东和曼哈顿区交界处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九十四街,那里的环境并不怡人,草木贫瘠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多大关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客人。那些日子,我总在焦躁不安地忙碌于自己的事情,忙碌于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当时的我总是把其他人看作是多余的干扰,不过我倒也并不是不喜欢和人交往。我还是乐于与那些波多黎各裔的邻居们用西班牙式的客套语寒暄上几句的。在下课回来的路上,我还会经常停下来与一群男孩子们攀谈一会儿,他们整个夏天都待在门廊上谈论尼克斯队,谈论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听到的枪声。要是赶上好天气,我和室友就会围坐在炉火旁抽上几根烟,欣赏暮色渐渐淹没了城市上空的蔚蓝。要不然我们就会看着那些住在旁边高档社区的白人到我们街区来遛狗,让狗在路边拉屎。这时,我的室友就会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大骂:“把狗屎弄干净,你这杂种!”在他们弯下腰去铲狗粪便的时候,我们就会面无愧色地嘲笑主人和狗。
每当那样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快乐,但那快乐只是暂时的。一旦谈论的话题偏离了主题,或者转向了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我就会找个理由起身告辞。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享受孤独的世界,因为我知道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就住在隔壁的老人,和我有着相似的性情。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偶尔外出时,人们就会看见一个苍老佝偻的身影,穿着一件厚重的黑色外套,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软呢帽独自蹒跚而行。有时候,我在楼下碰巧看到他刚从商店买东西回来,就会主动上前帮他把东西提上楼去,他会看看我,然后耸了耸肩。于是我们就一起上楼了,在每一层的楼梯拐角处他都要停下来歇一歇。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我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地上,他礼节性地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也不曾向我表示过一次感谢。
老人的沉默寡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心里我把他视作自己的同类。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我的室友发现他倒在了三楼的楼梯平台上,双目圆睁,已经僵硬的身体像个婴孩一样蜷缩着。人们纷纷上前围观,一些妇女在胸前画着十字,小一些的孩子激动地窃窃私语。最后,医护人员把尸体抬走了。警察到老人的公寓里进行查看――这是一间非常整洁的公寓,空空荡荡的,几乎什么都没有。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幅退色的妇人肖像,挂在壁炉架顶上。画中的妇人,眉毛浓丽,笑意温柔。有人打开了冰箱,在里面发现了将近一千美元的一叠小额钞票,这些钱都用旧报纸包着的,小心地藏在蛋黄酱罐头和泡菜缸后面。
这个场景弥漫着的孤独感触动了我,在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我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啊。然后,几乎与此同时,满怀着悲伤,我却又为这个愿望感到后悔。我感觉似乎这样的想法会破坏我们之间的灵犀――好像,就在那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那位老人正在低声诉说着一个从未向人提及的故事,正在向我讲述一些我宁愿不去听的事情。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十一月一个寒冷又阴沉的早晨,太阳被薄雾般的云遮住了,光线十分昏暗。这时,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当室友把电话递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早餐,炉上煮着咖啡,锅里煎着两个蛋。电话里满是静电的噪音。
“巴里?巴里,是你吗?”“是的……哪位?”
“喂,巴里……我是简婶婶。我在内罗毕。能听到我说话吗?”
“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你是?”
“我是简婶婶。听着,巴里,你爸爸死了。他出车祸死了。喂?听得清吗?我说,你爸爸死了。巴里,打电话给你在波士顿的叔叔,告诉他这件事。我不能再说了,好了,巴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
就这样,电话挂掉了,我跌坐在沙发上,任凭锅里的蛋烧焦,凝望着石灰墙上的裂缝,试图衡量自己的损失。
直到我的父亲去世,之前,对我来说,父亲更多的还是一个虚构的存在,仿佛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但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963年,我还只是一个两岁的孩子,他就离开了夏威夷回肯尼亚了。因此,作为小孩子的我,只能通过母亲和外祖父母讲过的关于他的故事来了解父亲。他们都有各自偏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因为讲过无数遍而无懈可击地通顺。现在我仍能回想起那些场景。晚饭后,外祖父斜靠在他那把旧式椅子上,啜着威士忌,用从烟盒上撕下的玻璃纸剔着牙,讲述我父亲因为一个烟斗而几乎将一个人扔下大风口的故事……
“是这样,你妈妈和你爸爸决定带那个朋友参观一下这个岛。所以他们就开车前往大风口,巴拉克一路上几乎都开错了边――”
母亲对我解释道:“你爸爸可算不上一个好司机,他习惯英国人的驾车方式,靠左边开车,而且如果你提出什么异议的话,他就会生气地嘲弄美国人的驾车规则――”
“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到了目的地,下了车,站在栏杆内欣赏风景。巴拉克用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烟斗抽着烟,用烟管指点着所有的景点,活像一个航行在大海中的船长――”
“你爸爸非常喜欢这个烟斗,”母亲再次打断了外祖父的话。“他学习的时候,整晚都要用这个烟斗抽烟,有时候还――”
“瞧你,安,你是要自己讲还是让我把这个故事讲完?”
“对不起,爸爸。你继续讲吧。”
“不管怎样,他那位倒霉的朋友――他也是一个非洲学生,是吧?他刚刚来到这里。这个倒霉的家伙肯定是被巴拉克拿烟斗的样子吸引住了,于是他问,能不能也让他抽一下。你爸爸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小伙子抽第一口烟的时候,就被呛到了,他不停地咳嗽。由于咳得太厉害了,烟斗从他手中滑落,掉到了栏杆外,落在了一百英尺深的悬崖上。”
外祖父停下来拿起酒瓶,抿了一小口。“嗯,当时,你爸爸非常有风度地等到他的朋友不再咳嗽了,才叫他爬到栏杆外把烟斗捡回来。那个小伙子瞥了一眼那个九十度的峭壁,然后告诉巴拉克他会给他买个新的赔偿――”
“非常可行。”图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我们称呼我的外祖母为图图,图是简称;夏威夷语的意思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在我出生的那天,她认为自己仍然很年轻,不想被叫做外祖母)外祖父皱了皱眉,但他决定当作没有听见。
“――但是巴拉克坚持要拿回‘他的’烟斗,因为这是一件礼物,无可替代。于是,那个小伙子又向下望了一眼,再次摇了摇头。这时,巴拉克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往栏杆外甩去!”
外祖父大喝一声,高兴地拍了下自己的膝盖。在他大笑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正注视着我的父亲,他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更为黝黑,那个冒犯他的小伙子被举了起来,乱晃着胳膊。多么可怕的审判情景啊。
“他并不是真的要把他丢到栏杆外去,爸爸。”母亲关切地看着我说,但是外祖父又啜了一口威士忌,继续讲他的故事。
“这时,其他人都开始来围观了,你妈妈恳求巴拉克放下他。我猜巴拉克的朋友只能大气都不敢出地祈祷了。不管怎样,几分钟后,你爸爸把那个人放下来了,拍拍他的背,让他平静下来,还提议大家一起去喝杯啤酒。你不知道,你爸爸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是怎样表现的――完全若无其事。当然,他们回到家之后,你妈妈仍然非常害怕。事实上,她几乎不敢开口跟你爸爸说话。而巴拉克也没有起什么帮助作用,因为你妈妈想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只是摇摇头开始笑起来。‘放轻松些,安娜,’他对她说――你爸爸是低沉的男中音,是这样的英式口音。”外祖父用下巴抵着脖子,追求完全逼真的效果。“‘放轻松些,安娜,’他说,‘我只是想让那家伙知道,对他人的财产要小心照看!’”
外祖父就又开始笑起来,直到他咳嗽起来,这时图就会小声地嘀咕着,她认为我父亲知道烟斗只是因不慎而掉落实在是件幸事,否则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母亲就向我眨眨眼睛,说他们都有些言过其实。
“你爸爸是有点跋扈,”母亲微笑着承认,“但是他本质上是个非常诚实的人,这使他有时显得不那么变通。”
她喜欢我父亲温和的一面。她会给我讲这样的故事。他穿着平时最喜欢穿的衣服去领取фBK联谊会的钥匙――牛仔裤和一件印着豹子图样的旧针织衫。“没有人告诉他那是一个多么高的荣誉,所以他进去之后,发现那个庄严的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身穿正装。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发窘。”
接着,外祖父会突然深思起来,开始自己点起头来,他会说:“这是真的,巴,你爸爸能够在所有的情况下胸有成竹,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都喜欢他的原因。记得那时他需要在国际音乐节上唱歌,是吧?他已经同意演唱一些非洲歌曲,但是当他到达时会场已经是一片骚乱。紧挨他之前表演的是一个半专业的女歌手,一个带着整支乐队的夏威夷女孩。其他人可能会就此打住,你知道的,然后解释说出了什么差错。但是巴拉克绝不会这样。他站到舞台上,面对着满场的观众开始唱歌―――我告诉你吧,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演出――虽然他唱得并不算好,但是他极其自信,于是很快像其他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外祖父会摇晃下头,从椅子上站起身,打开电视。“现在,你可以从你爸爸身上学到些东西,”他告诉我,“‘自信’,这是一个男人成功的秘诀。”
那就是所有这些故事的叙述方式――简洁明快,真实性可疑,一夜之间就能连续讲完。经年累月,这些故事就成为了我对家族的记忆,就像那些还保留在家中的父亲的几张照片一样,那是一些老旧的黑白冲洗照片,是我为了寻找圣诞节的装饰或者旧的潜水设备而搜遍储藏室时偶然翻到的。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已经开始与那个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谈恋爱了。无需任何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照片会被藏起来。但是偶尔,曾经和母亲一起坐在地板上,在散发出灰尘味和樟脑球味的破旧相册里,我一面仔细端详着父亲――露出灿烂笑容的黑色面孔,突出的前额和一副厚重的眼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 一面还听着母亲独自讲着他生平的事情。
我知道,他是一个非洲人,属于肯尼亚卢奥部落,出生在维多利亚湖畔一个叫阿兰戈的地方。村庄很贫穷,但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侯赛因・安扬高・奥巴马,是一位出众的农场主,他是部落里的长老,同时也是一个会看病的药剂师。我的父亲从小帮他的父亲放羊,长大后就读于英国殖民机构在当地设立的学校。在学校里,他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最终赢得了去内罗毕进修的奖学金;接着,在肯尼亚独立前夕,他被肯尼亚领导人和美国赞助者选中,前往美国大学深造,成为第一批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化非洲而到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并用这些先进技术建设家乡的非洲人之一。
1959年,二十三岁的他就读于夏威夷大学,成为那所大学里第一位非洲学生。他主修计量经济学,经过极其专心的攻读,三年后他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广交朋友,协助成立了国际学生协会,并担任了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一次俄语课上,他邂逅了一位羞涩腼腆的美国女孩。她仅仅十八岁,后来他们陷入了爱河。女孩的父母起先非常谨慎,但最后还是为他的魅力和聪慧所折服;这对年轻人结婚了,她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给这个男孩取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他获得了另一项奖学金――这次是攻读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带上新家庭一同前往。接着,分别的时刻来临了,他回到非洲去履行对那块大陆的承诺。母亲和孩子则留了下来,尽管距离遥远,但爱的纽带却不会因此而中断……
相册合上了,我却仍对听到的内容感到不解,我犹如置身于广袤有序的宇宙而迷失其中、不得其解。即使是母亲和外祖父母所讲述的简略版本,我仍然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很少追问细节,比如说什么是“博士学位”或者“殖民主义”,或者阿兰戈在地图上的位置等等。父亲的生活历程取代了母亲买给我的一本叫做《起源》的书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这本书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故事。其中,有关于《创世记》和人类在其下诞生的树的故事,普罗米修斯和火种的故事,还有漂浮在宇宙中的神龟背负着整个世界的印度传说等等。后来,当我可以从电视和电影中更快地找到乐趣时,我开始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了。是什么在支撑着神龟呢?为什么万能的上帝会让一条蛇造成那样的悲剧呢?为什么我的父亲不回来?但是作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我并不想解开这些谜团,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完整而真实的,能够让我平静地进入梦乡。
(《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美]巴拉克・奥巴马著,王辉耀、石冠兰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