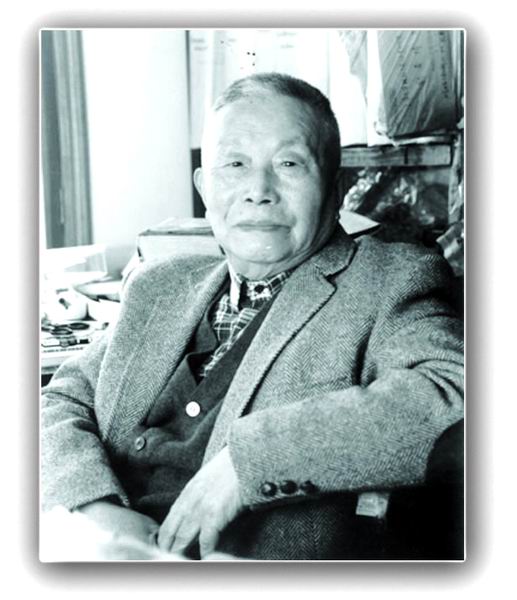
钱先生致力于翻译工作已经5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深居简出,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在德语文学的翻译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可以说,在健在的德语文学翻译家中,钱先生的诗歌翻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堪称一流的!根据我对钱先生的粗浅了解,我认为他的翻译业绩和治学精神至少可以概括这样五个字:即:专、诚、博、识、晓。
首先是“专”。这是钱先生翻译的最大特点。他不是把网撒得很大,今天译经济,明天译法律,后天译文学……文学方面他也不是一下小说,一下戏剧,一下散文。他的目标非常集中,主要专注于诗歌。我大略算了一下,他翻译的诗歌作品的数量,大概占了他全部译作的75%的分量。尤其在早期,在五六十年代,几乎全是诗歌:如海涅的《诗歌集》、《新诗集》、《罗曼采罗》、《德国诗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诗选》、《尼伯龙根之歌》等。文革后是《歌德抒情诗选》、《歌德叙事诗集》、《浮士德》、《席勒诗选》、《德国浪漫主义抒情诗选》、《尼采诗选》、《里尔克诗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荷尔德林诗选》等等。不错,他也译了一些散文、戏剧,甚至小说,但多半也是由于“爱屋及乌”,他实在太喜爱那些诗人了,因而把他们的散文里的精华也一起给译了!而这些诗人的散文确实也很精彩,所以就有了他译的《海涅散文选》、《里尔克散文选》、《尼采散文选》、《叔本华散文选》、《瓦莱里散文选》以及席勒的戏剧作品等等。这样专心致志于诗歌的翻译,不仅德语译界独一无二,别的语种也寥寥可数,而且他们在“专”方面也达不到钱先生的程度。因为他们都难免要写篇什么文章,或编一本什么书之类。而钱先生除了自己译本的前言后记之外,几乎就没有见过他写过诗歌以外的什么东西。其实他也不乏写诗的才能,事实上也经常写写,但那不过为了自娱自乐,或浇心中之块垒,并不谋求发表,以与翻译争锋。为了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腾出给翻译,他真正做到了“心无旁骛”。稍有点翻译经验的人都知道,文学的各类体裁中,诗是最难译的。要把它译好,摸出一套规律,确实需要你花费毕生的心血去琢磨。钱先生的这种专注精神,在译界是罕见的,堪称传奇。
钱先生翻译的第二个特点是“诚”。他对诗歌翻译的爱,爱得很诚,诚到“痴”的状态。大家知道,钱先生原来是学医的,已经在一家大医院工作了十几年,他也很爱他的专业,而且已经初露锋芒,小有成就,出版了几本著作。但是,当他一旦受到诗歌翻译的诱惑,跌入译诗的怀抱,就像中了爱神丘比特的箭,如痴如醉,忘乎所以,不顾一切,再也不能自拔了,以致连饭碗也“去他娘”了!根据科学的说法,一个人一生当中,一般只开发出10%的智慧。能不能突破这10%的界限,开发出更多的潜能,就看你有没有一股子傻劲:忘了擦汗,忘了饥渴,对各种诱惑都感到漠然,唯有对他的工作对象怀着不可抵御的兴趣,这兴趣推动他爆发出攻克一切的能量和耐力。我认为,钱春绮先生就属于这种人。想想看,“铁饭碗”在我们国家是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因而是个很诱人的东西,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扔掉一个很像样的“铁饭碗”而自谋职业,这意味着你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得不到医疗保险,失去了单位和集体对你的保护,这在那个年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因而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因此钱先生当时在这点上的表现,也是一个传奇。那么,钱先生为什么不要这个饭碗呢?医疗单位不尊重你的选择,但凭你五六本译作,在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另找一个饭碗,难道会有什么困难吗?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我想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按我的猜想,大概一个是为了换取更多的时间,一个是为了求得平和的心境。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个单位,会有很多?嗦事:经常要开会,要参加政治学习,要参加政治运动,要汇报思想,有点事还得请假等等。正像存在哲学家萨特说的:生活是“粘兹”的,是“令人恶心”的。现在回过头去看,确实,这一切跟翻译到底有多少相干呢?因此,钱先生当时的断然决定是明智的,不然我们今天就看不到他那么多的译作,说不定文革中他还少不了挨批斗。
钱先生的第三个特点是“博”。关于翻译我向来有一个观点,认为文学翻译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外语掌握要过硬。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不过硬,那么“信、达、雅”的第一关“信”你就过不了。二是母语功底要扎实。这也容易理解,因为文学是一门艺术,首先是语言的艺术,不仅语法要规范,词汇尽可能丰富,修辞还得讲究,从而使语言产生魅力。否则,你即使做到了“信”,却不一定能做到“达”,更不用说“雅”了。当然附带说一下,在对待“雅”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即原文是不是雅?如果原文不雅,你译得很雅,那就与“信”冲突了!三是知识要渊博。文学作品涉及天文地理,无所不包。知识贫乏,就会捉襟见肘,有时还会出洋相,例如把蒋介石译作常凯申。四是悟性要好。文学是想象的事业,想象如天马行空,无所约束,尤其是潜意识的“内宇宙”更是千奇百怪。翻译之难,难就难在经常遇到一些疙瘩,一些“节骨眼”,让人煞费苦心而不得其解,这时常常需要调动你的悟性。悟性就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一种“灵感”性的东西。只有悟性能使译文传神。以上四个要素无疑钱先生都是具备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第三点,即他的“博”。除了一般的知识丰富以外,他还表现在掌握外语的“博”。除了德文,他还通晓英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此外他还学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如果说,一般的知识丰富,不少人都能做到,多读点书就是了。但掌握五门外语,谈何容易!因为我自己也做过掌握四门外语的梦:英、俄、法和德语。我中学学了6年英语;大学第二外语是俄语;我夫人是科班法语。掌握四门有何难哉!不料,文革十年的荒疏,几乎连德文都忘光了!文革后,赶紧抢救饭碗,其他就顾不上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能改变这种独一无二的状况。可钱春绮先生也经历了文革,他为什么就没有荒废什么,五门外语门门在手呢?仅这一点,就让我非常佩服,也很惭愧。
对钱先生这样务实的翻译家来说,五门外语不是摆设。他是要派它们用场的。同行们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中国人单靠我们自己的知识背景,是对付不了欧洲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学范畴内的知识的,我们必须依靠外语。一门外语就是一个得力的帮手。在这方面钱先生显然比我们尝到了更多的甜头。他不仅通过它们翻译了一部分德语文学以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多门外语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典故、术语和词汇。纵览一下他的翻译历程就会发现,他越到晚年,不仅译文越练达,越精致,而且注释也越多越详尽,以致诞生了钱先生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的详注本。尼采的这部奇书,熔文学、哲学、美学于一炉,涉及到多门学科的知识,不加详注,则一般读者是很难完全读懂的。但以前的几个译本,有的一个注释都没有!有注释的也只有十几条而已,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而2009年出版的钱春绮先生的详注本,注释达1800条之多,约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除了田德望教授从意大利文译的但丁《神曲》那部创记录的详注本以外,我们德语文学的中译本中,迄今还没有见到第二部。这样的译本不仅具有阅读价值,而且还具有学术价值。钱春绮先生也因此堪称“学者型翻译家”。
在钱先生“博”的范畴中,除了多语种的长处外,还有国学的修养。这也是从我们这一代起所普遍缺乏的。钱先生小时候读的是私塾,《论语》、《孟子》等读得很熟,他尤其喜欢左丘明的《左传》,他自己说当时就背得“滚瓜烂熟”。难怪读钱先生的译作时,常感到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
钱春绮先生从事翻译的第四个特点是“识”,即见识。翻译队伍中常见的是两类人,一类是被动型的译者。他们对翻译的作品没有选择,有什么,译什么;出版社叫他译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另一种是自主性的翻译,他不盲目接受任务,他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说服出版社接受他的建议。这类译者具有战略眼光,具有远见卓识,他知道什么最值得译,什么最急需译,什么作品能够投合时代思潮,因而能够激起社会反响,因此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当年郭沫若就具有这种特点。他首先抓住德国最大的作家,“五四”时期翻译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第一部,他把准了中国社会的脉搏,一炮打响!其实他当时的德文水平并不高,他是学医的嘛,他还得学日文,还得学英文,还大量写诗,怎么可能有很好的德文?但他有眼力,他看得很准,这鼓动了他的勇气,所以一举成功。钱春绮先生也具备这种能够把握大方向的战略眼光,他把他相中的目标统统笼在胸中,然后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去实施。要知道50年代那时候,官方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西方古典文学一般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但钱先生看准了海涅和马克思的非同寻常的友谊,看准了海涅《诗歌集》中充满情哥情妹的内容被他《新诗集》中“我是剑,我是火焰”的锋芒所掩盖,他一口气译了海涅的三部诗集全被出版社采用。这位半路出家的医生,没有经过什么铺垫,一步就登上中国的译坛!紧接着他选编并翻译的《德国诗选》以及《尼伯龙根之歌》等译作进一步见出他的战略眼光!再加上近30年来所译的作品,则歌德、席勒、叔本华、尼采、里尔克、瓦莱里、波德莱尔、荷尔德林……,哪一个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沉甸甸的经典作家?
适合于钱先生的第五个字是“晓”,知晓、通晓的晓。翻译队伍中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因为自己懂诗、写诗、而且爱诗而走上译诗道路的;一种是自己不懂诗也不写诗而翻译诗的。钱先生属于前一种。他从小就爱好诗歌,14岁即开始写诗,16岁已集成诗集,而且一生也没有中断过,现在已经有好几本诗集了。只是他并不追求发表。写诗又爱诗,这是他在医学事业正顺畅的时候,毅然放弃医学而转向诗歌翻译的主要内驱力。而写诗、译诗的双向互动是二者互相促进的最佳方式。深入了那么多世界一流诗人的底蕴,怎么能不对他的诗歌创作不产生有益的影响?反过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怎么可能不对他的翻译实践如虎添翼?所以人们称颂卞之琳、冯至、绿原等人的诗译得好,无不得益于他们的写诗经验。这也是人们阅读钱氏译作时感到他的笔法娴熟、练达,节奏铿锵,诗味较浓的根本原因。这里随便举一个例子。他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尼采写到一处说棕榈树随风摇曳像女孩的舞蹈。他就想:棕榈树硬邦邦的怎么会像女孩的舞蹈呢?他查德文字典,Palme确实是棕榈树的意思。但他仍怀疑。后查日语字典,发现Palme也有椰树的意思;椰树斜着伸向海边,随风摇曳,就像女孩的舞蹈了!原来椰树一般的写法是Kokospalme,但有时Kokos是可以省掉的!这一事例既说明了钱先生的“博”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说明他的诗人的敏悟使他避免了错译。
钱春绮先生漫长的一生翻译工作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总结他的经验,显然不是这一篇短文所能解决的,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篇什来完成这一任务,以便让后人更好地来学习和继承。愿钱先生地下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