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达尔文年”已经过去,但达尔文在人类科学史、思想史上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一再回味。去年,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及《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国内出版了大量与达尔文及进化论相关的图书,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达尔文》。该书在国际上被
认为是最权威、最好的达尔文传记,但在国内却未受到读书界应有的重视。为使这本重量级译著不致埋没,我们特发表陈蓉霞女士的长文,以向读者推介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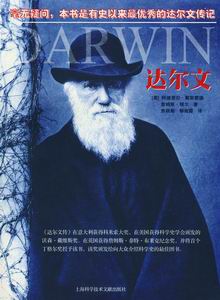 《达尔文》,[英]阿德里安・戴斯蒙德、[英]詹姆斯・穆尔著,焦晓菊、郭海霞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65.00元
《达尔文》,[英]阿德里安・戴斯蒙德、[英]詹姆斯・穆尔著,焦晓菊、郭海霞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65.00元
不同于牛顿,达尔文对人类心灵的冲击或许更有震撼力。如果说,牛顿在发现了万有引力之后,依然为上帝保留“第一推动”这一角色的话,那么,达尔文却通过自然选择理论废黜了上帝的这一角色;不同于引力理论,自然选择理论无须复杂的数学公式作为表达方式,就其字面意义而言,理解似乎不成问题,但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却需要跨越更大的障碍。不同于牛顿在一个奇迹年完成了他主要的科学工作,达尔文可说是穷其一生思考和完善他的理论。这就使得有关达尔文生平的读物更具可读性,《达尔文》厚重如砖头,却能让人读得津津有味,许多细节可圈可点,即是明证。
航海所见带来了诸多疑问,但最大的疑问却与人类有关。想到那些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他无法遏制这一念头:我们的祖先是否也曾如此?同一个造物主怎么会同时造出如此原始和如此复杂的人?一个线索逐渐浮现:各个物种之间存在一个亲缘谱系。联想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神创论的支柱也不再可靠:神所造的世界果真为人而存在?
自然选择理论的对立面是神创论或者说设计论。神创论中隐含了相互关联的若干命题:上帝造物;物种不变;物种背后体现设计者的意图;人类是创世计划中的最高一环;人类的荣耀或尊严直接来自神意。难怪当时的博物学家大多同时也是神职人员,因为博物学的最高使命就是为神创论提供证据。达尔文刚出道时,弃医学而入神学,原本就是打算做一个悠闲的乡村牧师,同时又能兼顾自己的博物学爱好。初入博物学的达尔文,曾经被当时英国神学家帕利的《自然神学》所打动。在帕利的书中,呈现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不同的物种各就各位,在这背后定然有一个设计者,而博物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寻找这种设计的证据,以便证明上帝的存在。
正是环球航行令达尔文偏离了原先设计的人生轨道。1831-1836年间,达尔文成为小猎犬号的乘客,起因是该舰舰长菲茨罗伊在航行期间需要一名绅士做伴,经达尔文在剑桥时的导师亨斯罗的推荐,家庭富裕、刚从剑桥毕业的达尔文有幸成为舰长的客人而获得这次机会。当然航行期间所有费用自理,包括考察费用,好在达尔文有个不差钱的富爸爸。
出航不久,达尔文做的第一个考察工作就是用网捕捉到无数微小的生命,它们形状各异、色彩斑斓,一个念头自然涌现:为什么广阔的海洋里有“如许美妙之物”却无人欣赏?将它们创造出来似乎没什么“目的”。(P89)这是对设计论投下的第一个疑惑。在南美这块新大陆,达尔文发现一种寄生黄蜂,它将刺死后的毛虫作为食物来哺养自己的幼虫。达尔文一直对这种低等生物无法忘怀,因为它的“恶行”似乎背离了造物主的“善”。
航行途中,达尔文收到了刚刚出版的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1832)。在第一卷中,赖尔讨论的是地球表面的逐渐变化。在第二卷中,赖尔讨论的则是,在变化的环境中,生物是否也会随之而发生改变。作者给出的结论是,环境的压力或改变只会让生物灭绝而非变化。联想到刚刚挖掘到的化石动物大地獭,达尔文对物种的绝灭印象深刻,但随着旧物种的灭绝,新物种如何产生却成了一个神秘的问题。这是达尔文首次模糊地接触这一课题。
1832年12月,军舰来到南美的最南端――火地岛,达尔文初遇传说中的野蛮人并且震惊无比,“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啊,甚至比野兽和家养动物的区别还大”。(P101)顺便提及,当时的小猎犬号上就有三位已经文明化的火地岛人,他们是舰长菲茨罗伊上次航行期间在火地岛带回的土著人,菲茨罗伊之所以承担这次航行使命,起因就在于想把这些火地岛人送回他们的家乡以便在当地传教。同样是火地岛土著人,但两者的差异却大相径庭,这说明了什么?这当然证明了人类本性的可塑性。这一事实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34年5月,军舰驰入南美的科克本海峡,对着那些“起伏不平、积雪覆盖的峭壁”,还有巨大悬崖下的一个小棚屋,表明曾有人迹在这儿出现,达尔文陷入了沉思。这是一片多么荒凉的自然,而人在这种环境中又是多么渺小,微不足道。在这里,人类“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主人”。(P119)这是对人类中心说的首次质疑。接下来的一年,1835年2月20日,达尔文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地震,大地突然颤动,许多人的生命瞬间被夺走。地震持续时间虽然只有两分钟,但它对心灵带来的冲击却持久而又深远。达尔文立刻联想到自己的家乡。如果这场灾难发生在人口密集的英国,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一幕。地震和火山爆发之类的灾害恰在提醒我们,人类犹如居住在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上方,或者在薄薄的冰面上滑行,其脆弱和不堪一击令人心悸,但这却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它成为达尔文思考物种问题的重要依据。终其一生,达尔文都在深刻思考痛苦问题。如果说,传统宗教正是因人生的痛苦问题而兴起的话,那么达尔文思考的结果却是抛弃了宗教信仰。因为神创论与生命的痛苦难以协调。
1835年9月,军舰来到南美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这块群岛如今已被认为是诞生自然选择理论的圣地。岛上盛产巨龟,在此的欧洲人认为,每个小岛都有各自独特的陆龟,以至看上一眼就能知道它来自哪个小岛。但这一重要的细节被当时的达尔文忽略了,他对此不屑一顾,以为这些陆龟是人们当作食物而引入的产物。但岛屿上的一种鸟类:嘲鸫,引起了达尔文的注意。它们似乎非常古怪,有些种类之间非常相似但又略有区别,他记录自己拥有两三种变种,而且“每个变种都只存在于自己的岛屿上-这一事实跟陆龟的情况相似”。(P133)但达尔文依然认为这些仅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在跨越太平洋期间,他不仅吃掉了那些陆龟,还望着厨师将那些意味深长的龟壳仍出船外。
南美大陆所特产的动物还向达尔文提出了这一问题,为何这里的有袋类动物和旧大陆的胎盘类动物截然不同?或许一个异教徒会这样想,“肯定曾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造物主在工作”,各自造出完美但独特的生物。然而这样的想法绝对是荒谬的,根据圣经,只有一个造物主。好在另一个事实有利于后者。达尔文观察到,一只蚁狮,隐藏在一个沙坑下面,抛出一股股沙子,将毫无警觉的蚂蚁带到它张开的双颚中。这种做法与欧洲蚁狮完全相同。难道两个工匠会造出完全相同的发明物?这只能证明地球上只有一个造物主。可见此时(1836年初)的达尔文,依然难舍神创论。
航海期间,1836年6月3日,达尔文还有幸拜会刚好住在南非的天文学家约翰・赫谢尔爵士。赫谢尔来此绘制星座图,已有两年了。赫谢尔不仅眺望星空,也关注大地。他如此批评赖尔,关于那个神秘中的神秘问题,即新物种如何在地球上出现,赖尔没有知难而上。如果地形在逐渐变化,而且引起这种变化的力量至今依然在起作用,难道不能设想物种也以同样的方式自然产生?这一问题对达尔文的震撼极大。《物种起源》要回答的正是这一问题。就在航海结束前夕,达尔文开始反思诸多现象,此时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陆龟和嘲鸫似乎有了某种意义。它们最初也许是来自附近的大陆,随后适应了各自的环境,于是其细微的特征仅与各自的小岛相匹配,它们是从同一个物种那里扩散而来的变种。如果情况确是如此,这将“破坏物种的稳定性,”并且有望解答赫谢尔那个“神秘中的神秘问题”。(P143)
环球航行即将结束,但达尔文的思想航程即将启航。航海所见带来了诸多疑问,但最大的疑问却与人类有关。想到那些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他无法遏制这一念头:我们的祖先是否也曾如此?同一个造物主怎么会同时造出如此原始和如此复杂的人?一个线索逐渐浮现:各个物种之间存在一个亲缘谱系。联想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神创论的支柱也不再可靠:神所造的世界果真为人而存在?
航海归来以后,达尔文请当时著名的鸟类专家古尔德鉴定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那些鸟类标本,结果令达尔文大吃一惊:尽管它们的鸟喙各不相同,但它们却是近亲。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欧文也得出了这一结论:化石大地獭和现代的树獭有着密切关系。达尔文不由得设想:为什么在任何地方,其现在和过去的生物都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事实全都指向物种的变异及相互间的亲缘关系。现在达尔文终于相信,每个小岛都有自己独特的陆龟或雀类,那是它们逐渐适应本地环境的结果,这就表明物种确实在发生变异,变异的结果是变种甚至新物种的出现。可惜的是,那些蕴含关键线索的龟却被达尔文吃掉了。就在形成上述看法之后,达尔文开始写下有关物种问题的笔记,那是在1837年7月。
1842年初,自然选择理论大致成形。过度繁殖和竞争导致“自然选择”,获胜者脱颖而出。生物彼此之间通过共同祖先而形成一个谱系。……现在达尔文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死亡、疾病等都是自然事实,与价值判断无关,与善恶问题无关。
在考虑物种演变问题时,达尔文断然否认传统的进步观。这是因为,变种的出现无非是适应栖息地的变化多端,这当中就不可能存在某种衡量进步的尺度。甚至人类自身的分化也是如此,野蛮人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表明他们很好地适应了这种环境。因而,“讨论一种动物高于另一种非常荒谬”,如果人类以理性的发达作为进步的标准,那么,蜜蜂无疑会以本能作为标准,可见这种比较毫无意义。由此可见,当后人把进化理解为进步时,实在是一种不幸的误会。顺便提及,达尔文一直用descent(世系)而非evolution来描述他的理论,直至《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版才出现evolution,这是因为他认为evolution一词已被滥用。
进一步深入思考,考虑到环境或气候的变化反复无常,那么,适应现象的出现必然也具有偶然性。想想一只小狗,生来就有厚厚的皮毛,在温暖的气候中它就会是个怪物,但若是在寒冷的气候中,它就会很适应。可见好与坏、适应与畸形都不具有绝对标准,而是与环境的变化有关。这又是一道智慧的闪电。
达尔文开始把目光转向人工育种。当时一位精明的鸟类育种家如此写道:“严寒的冬季,或者食物匮乏,就会杀死体弱多病者,起到品种选择的良好效果。”达尔文牢牢记住了这段话,并深刻体会到大自然残酷的一面。1838年9月末,达尔文拿起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书中关于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食物供应,从而导致弱者被淘汰的观点令达尔文怦然心动。大自然似乎类似于育种家,但比育种家更高明的是,她不只是关注个别性状,而是同时摆弄上百万的变异,确保更完善的个体脱颖而出。到12月底,达尔文承认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的类比是“我的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事实上,他把人工选择看作是寻找创世奥秘的钥匙,但这种做法实在令剑桥的教授们大跌眼镜。
又一个事实令达尔文若有所思。在巴西时见到过的一种寄生黄蜂有一种本能,它将一只毛虫麻醉并在其上产卵,这只毛虫即成为未来幼虫的食物。但在幼虫孵化之前,黄蜂已经死去。显然黄蜂不可能知道这种本能有利于自己的后代,它只是无意识地这样做,结果却是为后代的延续提供了保障。可见本能(或特定性状)的出现是随机的,仅当对生存有利时,它才会被选中并保留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思路。随着偶然性的引入,那种精心设计的神创论再次显得可疑。
1842年初,自然选择理论大致成形。过度繁殖和竞争导致“自然选择”,获胜者脱颖而出。生物彼此之间通过共同祖先而形成一个谱系。上帝通过这种方式令无数物种自然创造,而非通过个别创造的方式。如此我们就能设想,死亡、饥荒、疾病等都是上帝创造物种的方式,或者说是自然规律的体现,上帝无须为这种罪恶负责。现在达尔文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死亡、疾病等都是自然事实,与价值判断无关,与善恶问题无关。
由于航海期间收集的诸多珍贵标本及其发表的地质学见解,他在学术界已声名雀起;但在私下里,他却在从事一种危险的研究,它不仅冒犯亲人和朋友的感情,而且还将危害社会的正当秩序。达尔文因此而身心交瘁,这或许正是他一生深受病患折磨的原因。
其实在达尔文的思路中,物种起源与人类的起源本是同一个问题。但说到人类的起源,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人类的道德感难道也是通过自然选择而非神授?对此,达尔文也早有思考。达尔文的父亲是个医生,接触过不少病人,伴随着躯体疾病,这些病人往往还表现出情感上的障碍。这让达尔文想到,情感或精神,或许正是大脑的功能。正如引力是物质的属性那样,思想为何就不能是大脑的分泌物呢?人类不愿承认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们的傲慢,我们的自我崇拜”。(P191)“傲慢的人类自以为是神的产品,值得神的干预,我却相信人类更卑微,是从动物中产生的。”(P193)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想方设法寻找证据。于是,他关注表情的起源问题。当时已有人提出咧嘴笑最初的意图是用来展示犬牙的,但却遭到抨击。达尔文深入探究,认为它“无疑是从以前拥有巨大犬齿的狒狒遗传而来的习性”。这一设想已经得到如今社会生物学的支持。1839年12月,达尔文的长子威廉出世,达尔文就此记下婴儿的一颦一笑,以此搜集人类表情先天性的证据。达尔文的妻子爱玛知道他有此研究癖好,曾如此打趣:也许在你眼里,我只是一个研究标本,当我心情不好或发脾气时,你却在构思一个理论:这证明了什么?事实上,就在达尔文向爱玛求婚之际,他确实如此问道:当一个男人说他爱某个人时,他脑子发生的是什么?达尔文的这一追问在今天终于有了答案,无论是性还是爱,确实都与某些特定的激素有关。
如果说,思想源于大脑的功能,而大脑(神经系统)的活动又受无情的自然规律所支配,那么,思想或意志怎么可能取得自由?然而,意志自由不仅是哲学的立论,更是神学的支柱,因为自由意志不仅与神授有关,而且还保证了道德的可靠。因此,得出这样的推论连达尔文本人都感到极度害怕。但休谟也正是站在同一立场上反对自由意志说的,达尔文曾经熟读休谟的著作,很难说他没有受到休谟的启发。
若是如此,道德从何而来?达尔文认为,仅仅从群体本能中,他就能够推出“所有最美好的道德情操”。想想哪怕是一条狗,它的行为也符合群体规则,而道德的功效无非就是令个体的行为与群体的规范相协调。因此,良心的起源,不是来自圣经的教诲,而是来自我们动物祖先的亲情。
思考物种起源问题,对当时的达尔文来说,有时不啻是一种痛苦的磨难。因为他的上述异端念头只能写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若是公布于众,由此引起的后果实在难以想象。比如假设承认精神就是躯体的产物,岂不意味着人死后灵魂不灭的教义荒谬不堪?因此达尔文可说是生活在一个双重的世界里。由于航海期间收集的诸多珍贵标本及其发表的地质学见解,他在学术界已声名雀起;但在私下里,他却在从事一种危险的研究,它不仅冒犯亲人和朋友的感情,而且还将危害社会的正当秩序。达尔文因此而身心交瘁,这或许正是他一生深受病患折磨的原因。
然而,达尔文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或许他知道自己的理论难以被顽固的学术界前辈所接受,但却有可能赢得一个后起之秀的认同。于是他向年轻的植物学家胡克透露了自己正在研究的内容,并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尤其是在植物学方面。事实证明,胡克后来不仅接受了进化理论,而且成为达尔文的得力干将。胡克曾于不经意间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学者若是“没有详细地描述过许多物种”,那就没有资格“研究物种问题”。(P261)说者无心,听者有心,为了取得这一研究资格,达尔文开始关注一种不起眼的小生物-藤壶。起初达尔文以为几个月就能搞定。但意想不到的却是,最后达尔文花费了8年的时间(1846-1854),才完成这一工作。幸亏当年达尔文不需要申请课题资助,否则他就没法顺利结项了。
这一艰巨的工作不仅为达尔文赢得了研究物种问题的资格,更为他提供了有关物种进化的宝贵资料。他曾经认为变种是自然界的例外,但藤壶彻底改变了他的这一看法。形形色色的藤壶物种都是“不同寻常的变异”,其各个部位都很容易变化,他越是仔细查看,物种的稳定性就越像是错觉。有时,变种和物种的界限难以分辨,以至“作为思考者,这让我感到愉快;但作为分类学者,却让我感到讨厌”。(P287)
终其一生,达尔文从未在公开场合抨击过宗教,尽管私下里,自从爱女安妮夭折后,他再也不去教堂。这不是达尔文的软弱或妥协,而是他的策略。……事实证明,达尔文的策略明智且有效。其实达尔文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明智和稳妥,又何尝不是英国民族的精神财富呢?
赖尔尽管不支持达尔文的理论,但他还是善意地提醒达尔文,应该写出来,以免被别人抢先。这可不是空穴来风,一位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已经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并获得好评。不过当时的达尔文还看不上论文中所表达的肤浅观点。1858年6月,华莱士的另一篇论文直接寄给达尔文,达尔文顿时有措手不及之感。因为这篇论文所表达的观点与达尔文正在研究的内容高度一致。眼见20年的艰辛研究到头来却极有可能让别人占先,达尔文的沮丧难以形容。幸亏有胡克和赖尔作为证人,达尔文才不致功亏一篑。在他们两位的安排下,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被安排在林奈学会上同时宣读。同时,达尔文也加快了出版步伐。1859年11月,物种起源终于问世。
尽管达尔文和华莱士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提出者,但两人尤其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却存在严重分歧。不同于达尔文,华莱士在南美采集标本时,曾经与土著人同吃同住,因而对那些土著人极其尊敬,这就不同于达尔文对土著人的看法。在华莱士看来,自然选择只能针对实用能力,而土著人的智能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实用所需,因而不可能通过自然选择得到,只能是神授。进而言之,人类的精神能力也只能出自于神授。达尔文当然完全不能认同这种观点。
1859年6月,当时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曾经向维多利亚女王建议授予达尔文以爵位,赖尔已经获得爵位。阿尔伯特亲王也赞成,因为他是科学界的朋友。由此可见当时达尔文的名声。但随着《物种起源》的出版,女王的教会顾问们,包括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迅速加以制止,因为授予这一荣誉则意味着对此学说的认可。于是,此事不了了之。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达尔文的贡献远在赖尔之上,但世俗的名声却给了赖尔。
不过达尔文也有其精明之处。达尔文在美国有一个忠实的粉丝阿沙・格雷,一位自由主义神学家,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三篇支持达尔文的文章,同时他还认为“自然选择与自然神学并非不相容”。达尔文很高兴,出资让这些文章装订成册,并进口了250本到英国,还把其中的100本送给科学家、评论家和神学家,其中包括威尔伯福斯主教。尽管他很乐意推出这本从宗教上认可《物种起源》的小册子,但当他后来再写书时,却试图说服全世界的格雷们相信自然选择其实是自发的,并不依赖上帝。
终其一生,达尔文从未在公开场合抨击过宗教,尽管私下里,自从爱女安妮夭折后,他再也不去教堂。这不是达尔文的软弱或妥协,而是他的策略。他说:“自由思想最好通过逐步启迪人们的心智来发扬,而这又产生于科学进步。因此我的一贯目标是避免撰写有关宗教的论述,把自己的范围限定在科学之内。”事实证明,达尔文的策略明智且有效。其实达尔文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明智和稳妥,又何尝不是英国民族的精神财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