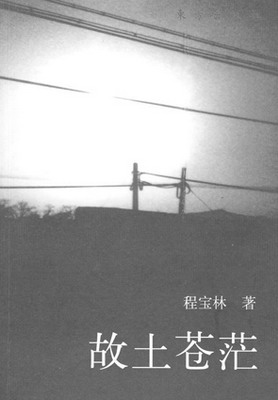
《故土苍茫》,程宝林著,东方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26.00元
“越来越多的人家搬走了,土屋被拆掉,只剩下断墙残壁。连以前热闹喧哗,孩子们
近些年来,程宝林身在夏威夷岛上的某个大学教书,孜孜不倦的却只有一件事:还乡。他手里捏着一张张机票,辗转在中美两国的各大机场,或手里握着电话,一次次拨通同一个熟悉的号码;没有青春做伴,亦非衣锦还乡,引导程宝林的只有经年的孤独和乡愁,而唯一的行李则是他那不改的乡音和斑白的鬓发。他要回去的地方叫歇张庙村――江汉平原上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子,因为养育了一个叫程宝林的孩子,它正在和即将拥有一部自己的村庄史。
犹记得十几年前,我和程宝林共事,在四川的一家党报做记者,我们毗邻而坐,共同面向窗外喧闹的蜀都大道。有时候我们会把工作丢到一边,摆摆龙门阵,唠唠家常。我们的话题常常离不开两种,一个是农村老家的命运,一个是来自农村的孩子进城后该怎样保持朴实的心态,如何不在城市的虚荣和繁华中迷失方向。我们的共识就是读书。我们都是被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农村孩子,也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在城市的处境。这是我和程宝林之间的默契,也是多年来维持我们友谊的一条纽带。在我眼里,程宝林是一个温和的兄长,沉静的读书人,浪漫的诗人,也是一个固执得近乎迂腐的书生。他由鄂而京,再由京入蜀,他自然地违背“少不入川”的古训,娶了漂亮的妻子,生了可爱的儿子,但是他并不打算将这古老的符咒一念到底――天府之国的安逸和闲适留他不住,成都平原的温柔富贵在他是羁绊和沉沦――他成天抱着英汉词典背单词,一心一意地想带着妻儿去美国念书。他相信读书会再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命运,让他经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多年过去,他梦想成真,以中年之身取得艺术学硕士学位,又在夏威夷某大学谋得教职,用他的话说:“靠汉语,更靠英语,挣一碗洋饭吃”。仅这一点,已经让他感到满足和自豪。
他初抵美国时做过停车场的保安,当过保姆,经历过没有房住甚至没有被褥庇寒的尴尬――这些我都是在《故土苍茫》里读到的,这多少让我有些吃惊。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和程宝林互通邮件,他跟我谈的都是读书的事情,在他尚未脱离困顿的2003年,我还收到过他寄来的几本美版文学书。在他看来,生活的艰辛与求学的喜悦相比微不足道,“到美国留学,获取一个美国学位,在我,是一个既微小、又遥远的梦想。虽然只是一个硕士学位,我感觉良好,深为自己感到骄傲。”(《骊歌起处紫衿飘》)程宝林也乐于展示这种骄傲,把自己42岁毕业于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消息贴到家乡湖北的网站上,竟然遭到嘲笑、攻击和蔑视。为此,程宝林深感迷惑。在读书这件事上,程宝林永远跟孔乙己一样不能释怀。
程宝林不被理解的还有写作。因为他写的文章,他涉及的题材,他关注的人和事,始终是那生他养他让他想念让他痛心让他眷顾和魂牵梦萦的故土和故人。他在海外一篇篇地写,一篇篇地发表,又集结成书,在《故土苍茫》之前,已有一部《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出版,为此他被人戏称为“农民作家”。或者,这是一件让人看不惯的事情,一个喝洋墨水说洋文吃洋饭住洋房以拥有洋文凭洋国籍为骄傲的中国人,却把满腔的情感寄托在一片早已被自己抛弃的土地上――而为了离开它,摆脱它赋予自己的命运和桎梏,程宝林付出了半生的代价。这或许正应了一种宿命:如果漂泊是诗人的宿命,那么还乡便是诗人的天职。程宝林的人生被分成了两部分――前半生离去,后半生归来,它们的总和,便是一部《故土苍茫》。
与其他诗人的回归不同,程宝林的归途是现实而务实的,他虽然是诗人,却把诗意主动清除出了行囊。他从村头走到村尾,提着烟酒,捏着红包,挨家挨户挨个拜访,他让记忆唤醒每一个村民,活着的、远走的、死去的,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坐下来交谈、回忆。于是就有了一篇篇动人的文字,《故土苍茫》、《屋前宅后》、《回家吃饭》、《父母的“批判”》、《布衣自有忧国心》、《祖坟》、《祖屋》……程宝林的写作,有诗人式的悲悯,包含哲学和人文思考,有记者式的批判,既客观又冷静,同时也是农民式的,务实而且准确,他认真地记得每一种关系,屋前宅后,左邻右舍,远亲近戚,新朋旧友,那些微妙的乡村人际,那些恩恩怨怨,你来我往,像一幅幅地图,深深地镌刻在程宝林的脑子里,以至于时隔多年,他也能一一撷取,并写进文章里。我真佩服他的好记性。比如他依然记得高考的成绩是81分,父亲从农村带到成都的粑粑有20个,20年前沙洋的老友付的餐费足足有50块。如果说程宝林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是白描式的,《故土苍茫》则是写实的,在故乡面前,程宝林是诗人、记者、知识分子、农民、学生、作家,但更是一个漂泊多年的游子,他带着复杂的情感,仔细地打量这残酷的村庄现实:物非人非景非。
“为什么我不能为这个村庄写一本《村庄史》?在这本只涉及一个中国小村的断代史中,我要发扬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让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传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这些如蝼如蚁的生命,曾经承载了一个中国的时代。那个时代,无情地夺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留给他们的是两代人的赤贫,是如今的断墙残壁、冷清无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亲种下的蔬菜。”于是,为故乡写史,就成了程宝林自觉的使命。但这个看起来微渺的工程因为隔了太平洋的浩瀚波涛而变得艰难和沉重。因为程宝林的归程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更是精神和历史意义上的。在面对村庄兴衰的同时,他必须也要面对自己的家庭,包括他自己――因为他以及他的家,也是村庄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程宝林把歇张庙村放进一个广阔的时空,看它在一个乡镇,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中如何辗转变迁,如何繁荣,又如何衰败,而他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不过是在为故乡的历史做一个生动的注解。“兄妹六人,全部跳出了农门,他这个长孙甚至举家移居到了美国,父母也搬到了城里,开始学着当城里人。旧宅倾颓,家园荒芜,而我的内心是何等的欣然啊!”这是程宝林的家人苦苦奋斗出来的幸福感,也是歇张庙村人迄今为止创造出来的最高标准。但是程宝林也知道,自己错了。“花两代人的努力可以摆脱农民环境和农民家庭,不易,要想在思想观念上和生活习惯上摆脱农民的价值判断,这不是两代人可以完成的任务。”(《父母的“批判”》)这是程宝林要面对的一种痛,而更大的痛还在于,在一个农村家庭的出类拔萃背后,往往是一个村庄的没落与衰败的开始,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漂泊时代的到来。
所有的路都通向城市。这是谁都逃不过的时代,我们跟程宝林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以读书、理想、打工、挣钱的名义,从千万个歇张庙村,从千万个沙洋县城,从西部、北方向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迁移,我们丢下老人与小孩,任田园荒草萋萋,家宅塌颓,我们身上打着农业文明的烙印,如今又再加上工业文明的镣铐,我们在城市和乡村,国家与农民,土地与饭碗,语言与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在时代的华丽转身之中华丽转身。然后我们累了、倦了、老了,我们返乡,却发现我们回不去了,故乡面目全非,我们无家可归。在出逃与回归的迷途中,程宝林是清醒的,也是体贴的,他抛开中年返乡的种种伤感和喟叹,以一个农民儿子的本分和孝顺,为父母了却多年的心愿,“将几间早已废弃、东倒西歪的土屋拆除,新建了三间瓦房。父母故土难离,田园难舍,又从100多里外的城里搬回家中,成了村里唯一没有责任田的‘编外村民’”。
我相信,那三间新的大瓦房,在歇张庙村无疑是最有生机和最漂亮的建筑,它们将是程宝林父母安度晚年的最好场所。我也相信,程宝林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也找到了安妥灵魂的大地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