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雷颐 时间:2006年10月25日 地点:北京第三极书局
|
■特约主持人开场语 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语言,有了语言,我们才可能交流思想和知识,而语言的背后又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时代的精神。语言既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又使人类摆脱了一个个单独的个体的存在模式,使相距千千万万里的人们、使相差千千万万年的人们合成一个群体,使后来的人类,可以不断地站立在前人的肩膀上,从而成为巨人。 在语言的发展、交流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规律,语言怎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们又应该怎样对待语言交流带来的文化通融?雷颐先生是研究历史的,他将从近代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给我们解释这些问题。 |
雷颐:各位朋友,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互相探讨这个问题――语言的力量。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当然以近代中国的新词为中心。大家知道,在人类的相互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而语言本身又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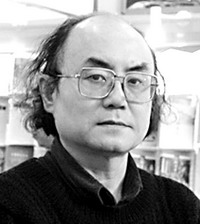
简历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小学还没毕业“文革”开始,于是下乡插队当农民,当兵,当工人。1978年考上大学,1982年考上研究生。于是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著作有《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等。译著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一、语言的发展能导致社会的变化
语言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新词汇的产生,新词汇表示新事物的引进,新事物包含着新知识,新知识孕育新的话语体系,这些将导致社会的变化





在梁启超、邹容、陈天华等人的著作中,革命、自由、时务等词语被赋予新的内涵,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大家知道,语言的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之一就是新名词的产生。一种新名词就表示一个新的事物。人们在和别的民族交往过程中,不断会传递一些新的词汇。这些新词传进来以后,往往有几个层面的意义:最表层的就是表现新事物、新知识。比如我们现在在这里用麦克风,“麦克风”就是一种外来的新事物,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事物,你必须用这个新词描绘它,给它进行定义。那么在这个表层面之下,还有进一步的意义,就是一种新的知识。人在麦克风之下说话为什么声音这么大?现在声、光、电繁荣知识告诉人们声波怎么转化成电磁波等等,这是一种新的知识。再进一步说,在这种新事物、新知识之下,还有一个层面影响更深远,就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价值体系,用现代的话说叫新的话语系统,这是更重要的!附带说一下,“麦克风”是最早的音译,后来改用“话筒”,“麦克风”几乎已从我们的语言中退出,但现在人们又开始越来越多地用“麦克风”,还发展出“耳麦”、“麦霸”等等。同样,“巴士”也是一种车的音译,早已被“公共汽车”、“面包车”取代,但现在又“卷土重来”,有“大巴”、“中巴”、“小巴”,还有的城市成立了“巴士公司”。从这种音译词的消失到重现,如果仔细探究,后面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呢。
比如说近代引进的一些新词:“科学”、“民主”等,这与中国传统的格物、民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话语了。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党”,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汉语里也有,但那是一个很负面的意思,直到今天这种负面的意思在语言中也还存有遗迹,像我们说“君子不党”、“结党营私”,“死党”等。但是,党这个词在近代从外国引进后,就相当程度修改了中国传统汉语中“党”这个词汇的意义。“党”这个词几乎完全成为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一套话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又如劳动、劳动者、劳动阶级、劳动神圣这些词,对中国近代政治、对鼓舞人民参加社会活动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我还要特别说说“革命”这个词,因为以“革命”为代表的这套话语是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化的一个助燃剂。
梁启超在1902年专门写过“释革”这篇文章,他说汉语“革命”含有英语Reform和Revolution这两个意思:Reform是根据一个事物本来的面目而进行的一些改良、改善,比如像英国1832年的革命实际上就是Reform。而Revolution的意思则是像轮子一样,把一个事物完全颠倒了,比如说法国1789年的Revolution就是革命。梁启超当时在日本,日本人把这两个词分别翻译成改革、革新和革命。日本人借用了汉语中“革命”这个词,但汉语中提到的革命是指王朝的易姓,新王朝推翻了一个旧的王朝,所以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1904年的时候,梁启超又写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他把革命分了三个层次,认为革命有狭义、次广义和最广义三个层次:最广义的革命是指社会上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所发生的大变化,不论是观念的、物质的,还是一个制度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动;次广义的革命就是指用暴力手段,用一个新时代取代一个旧时代;最狭义的革命是指专用兵力来推翻中央政权。
现在“革命”已是一个常识性的词,但刚刚引入中国的时候,人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梁启超就对革命这个词做很多解释。
刚才这几个例子说明,新词的引进,实际上就是一种新事物的引进,新事物包含着新知识,新知识之下孕育一种新概念、新的价值体系、新的话语体系。这些新的观念、新的话语体系必将导致社会的变化。现在我们语言中的“党”与传统的“党”完全不同,所说的“革命”与传统“成汤革命”、“汤武革命”中的“革命”完全不同。新词引进说明,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不同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
二、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是不均衡的
语言是非常“势利”的。在实际情况中,语言的影响主要是单向的,即从经济、文化、政治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
我们知道,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甚至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都各有各的语言,像咱们国家就有许多方言。随着人类交往的增加,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但是通过研究语言互相影响的历史就会发现,语言的影响并不均衡。从语言影响的强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弱,或者可以称之为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软力量”是强还是弱。
|
|
|
日文的假名写法来源于汉字的草书,可见汉语对日语的巨大影响。 |
第一,人们从心理上愿意使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
经济文化发达,这个民族或地区所用的语言有优势,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就受它的影响;反之,落后地区的语言、方言很少能影响经济发达地区。比如今天我们称东亚的一部分地区为“汉字文化圈”,因为过去像朝鲜、日本这些地方都使用汉字。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发达、文化灿烂,比其他国家强,所以中国的文字、语言就影响了它们。
再举一个例子:东晋的时候,那些“南渡”的贵族、士族以说洛阳话为荣,歧视当地的吴语,因为吴地当时不如中原文化发达,说洛阳话一方面是思乡,一方面是“雅”的象征。但现在,“吴侬软语”已不再被当作低级、落后的象征了。
现在好多外乡人到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想在那儿扎根,就要尽量说上海话和带着京味儿的普通话。当然也不是只有中国这样,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也经常写到外省的青年到巴黎去奋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就要尽量脱掉外省的口音,变为巴黎口音。以前俄国的贵族都是以说法语为荣的,他们彼此交谈都要说法语。他们就是说俄语的时候,都故意有一点法国腔。贵族家庭都要请法国家庭女教师,以至旧的俄国小说中经常的情节是家庭男主人与法国女教师的暧昧关系。我记得著名的小说《安娜・卡列妮娜》好像就是以女主人公哥哥和法国家庭女教师的暧昧关系引发家庭矛盾,她去调解引发开头的。为什么俄国贵族要说法语呢?因为他们自己都认为,在当时世界上,或者说在欧洲文化圈里面,俄国的文化不如法国的,所以他们的上层人以说法语为荣,作为身份的一个高贵的标志。现在你到北京“国贸”附近的咖啡馆坐坐,就会听到那些“白领”们说话时不时夹杂英语。
这种心理,你可以不喜欢、不赞同,甚至说是“不健康”,但千百年来就是如此。
第二,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更容易大面积流行。
英语是现在公认的“强势语言”,但其中许多音乐方面的词汇,却是来自意大利语,说明意大利音乐的发达,英语再强,在这方面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从中吸取词汇。
再比如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它的方言词汇就有可能进入普通话,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例如我们经常用的“寻开心”、“阴阳怪气”等,原来都是上海方言。北京是“首善之区”,京话当然更容易在全国流行,随着电视的普及,一些带有北京特色的文艺作品在全国流行更快,于是那种北京街头巷尾的语言和一些北京方言,也更快在全国流行开来。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快,于是粤语北上,形成了粤味的普通话:吃完饭了“埋单”,把一个事情“搞定”,还有“生猛”、“炒鱿鱼”等等。我1984年到广东出差的时候,见到很多美发店有一个字是“?”,不知道念什么、什么意思,查字典才知道就是“蒸”的意思,现在北京的大街上满街都是“?油”、“盐?鸡”什么的,没有写“蒸油”、“盐蒸鸡”的。有意思的是,“埋单”被普通话改造成“买单”,一些广东人反而认为“破坏”了粤语的“纯洁”,提出抵制、反对,说是要“保卫粤语”。我开玩笑说,这些年粤语对普通话的“破坏”还少啊!这种只允许粤语“破坏”普通话,不许普通话“破坏”粤语的观念,与许多人认为这些年粤语大大“破坏”了普通话的“纯洁”性,所以要抵制、反对粤语的观念一样,都是“语言原教旨主义”。
事实说明,只有政治、文化中心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才有可能“大面积流行”,它的一些词汇才可能成为官话、普通话的一部分,而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语言只能是边缘,很难登大雅之堂。
第三,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的词汇、语言,需要一种权威的认可才能进入主流语言。
上面两种是通常的情况。大家可能会提出反对的例子。比如我国的东北农村经济文化就不十分发达,但像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小品演员却很了不起,把一些东北土话,像“忽悠”这个词,楞是靠自己的表演、自己的才华使其逐渐成为全国的流行词汇。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赵本山的语言在电视小品中本是作为“笑料”出现的,也是通过中央电视台这种权威的认可,才开始在全国流行的。这就说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词汇、语言,要想进入中心,成为流行语、普通话的“一分子”,实际上仍要经过文化中心的认可之后,才能够进入主流语言中,这时才能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三、中国近代的新词是怎样登上历史舞台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一种新的挑战,这时候中国开始一点一点地接受了新的词汇,新词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
|
|
|
|
京师同文馆旧址 |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内景。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些翻译机构担负起了为中国引进国外科学技术知识、翻译国外科技文献的重要任务。 |
咱们现在要讲一下中国近代的情况。在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圈之内,中国文化确实是最优秀的,所以中国认为我就是天下,我就是世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一种新的挑战,这时候中国开始一点一点地接受了新的词汇,新词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
1.反对者也不得不使用新词
新词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也是往往被别人作为笑料的。比如当时有几句打油诗:
“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间接也风流。”
“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
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笑的。但当时“团体”、“脑筋”、“目的”、“精神”、“中心点”、“以太”、“方针”这些词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词”。这些新词进来的时候确有很多人嘲笑,曾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现在人觉得一点不好笑的词汇,在当时就被认为十分可笑。
湖南有一个保守派人士叫叶德辉,在维新运动时就痛斥这些词,提出来要辨文体,他指责说:“异学之?词(按:?音“毕”,?词指邪僻的言论)、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诡僻,不得谓之词章。”当时维新运动在东南影响比较大,维新派的报纸上这些新词汇用得多,他认为这种文风就不能成为词章。
另外两个例子更有名:当时清朝的大员中有一个张之洞,以开明著称,但就连他也反对用新词。他有一个姓路的幕僚,一次帮他起草文稿时用了“健康”这个词,张之洞一看这个稿子勃然大怒,批了几个字就把这个稿退回去了。他说:“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得可恨”。这个姓路的幕僚对新词比较了解,他写了几个字将文稿又交了上去:“名词乃日本名词,用之亦觉可恨”。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的端方,在一次批阅学生“课卷”时写到:“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他不知道,“思想”、“组织”也是新名词,因此成为一时笑谈。
反对用新词者如张之洞、如端方,也无法摆脱新词,历史的舞台上这些新词不可避免地登场了。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俄罗斯的谜语:不是蜜,但是能黏住一切――谜底是“语言”。
2.近代中国通过日本来了解西方,这表现为对日本新词的引进
甲午战争之前,哪怕是先进的中国人,也看不起日本。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日本打败,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1900年前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赴日,由于中日同文的原因,日本习惯用汉语的词汇翻译西方的词汇,这些词又被那些留学生大量带回中国来,因此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西方书籍,远远超过了当年中国人直接翻译的西方著作。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写了一篇文章说,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样你才能掌握西方的新词汇、新知识、新观念。他说自己住日本数月,开始学日本文,读日本书,才能见到从前没有见到过的那么多书。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梁启超应该是中国新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但他通过在日本的学习,竟觉得自己就好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突然看到了光明”,在“很饥饿的时候突然有一顿酒肉”的感觉。过了几年梁启超又写文章回忆他在日本的经历。他说在日本一年后使自己的“脑质”为之改变,思想言论与前者相比好像两个人。梁启超原来写文章多数是用中国的术语,从日本回国后就改用日本的新词。所以他说社会的事物越来越复杂,新事物的出现就会有新名词的出现。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意境出现,就会有一种新的名词来描绘它,来定义它,来传播开来,新新相引才能不断的进步。
1900年以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都集中在日文书上了:当时差不多每一所日本学校的教科书都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日本教员的讲义都翻译成了中文书。大家知道百科全书对知识的分类是有一种规范作用的,这个时期中国也把日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其中发行最广的是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影响不小。这套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六种,文学一种,教育五种,政治法律十八种,自然科学二十八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二十二种,其他两种。这套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有一个大翻译家严复,在近代新知识、新思想的引进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新词,很快就取代了严复翻译所用的词。如严复翻译了穆勒的《逻辑学》,但他没有用“逻辑”这个新词,而用了中国传统的“名学”一词,翻译成《穆勒名学》。后来人们从日本引进“逻辑”这个词,很快就代替了“名学”。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经济、哲学、服务、组织、纪律、后勤、健康、商业、干部等等。现在我们说话有太多的词都是当时引进的新词,如果现在统统把这些词排除出去,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可见这些新词对我们生活影响之大。
以上以点代面,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近代中国新词汇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正如梁启超所说,有新事物、新思想,就会有新词汇。
四、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语言
对新词主观抵制行不通,而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语言的发展,并不会导致我们传统文化精华的萎缩

外国留学生在学习中国书法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刚才我们了解了近代中国以新词为代表的语言发展过程,这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1.片面排斥的历史教训
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是先于日本被西方打开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实际上也先于日本。日本在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还通过中国来了解西方,比如铁路、铁道,公法、选举,化学、细胞等词汇,就是日本从中国引进的。后来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日本,反而不得不从日本大量引进新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整个社会在近代开始的时候对西方的语言及其带来的知识,采取一种抵制、排斥的态度。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作为有见识的中国官员,就开始广为搜集西方各国的材料,并让人编《九洲志》,翻译了一些关于世界地理的书。他还利用华侨搜集了大量的西方的报纸进行翻译。但是他的这个工作却受到了从上到下的排挤,当时大多数官员认为林则徐破坏了中国的文化,让狄夷的东西影响了中国。后来林则徐把收集的材料交给了好友魏源,魏源整理后编成了《海国图志》。《海国图志》着重介绍了外国的机器、先进的武器,并提出了“师夷长技”的观点。结果很多人看了这本书感到震惊,认为是宣扬狄夷之技加以排斥,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也没受到重视。但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在短短几年内就翻印了21版,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大家看,林则徐、魏源编写这本书是为了启发国人,但是他们受到了国人的排斥;相反日本人对此书如获至宝,经过明治维新变得强大了,反过来又侵略中国。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对新语言及其带来的新知识,如果片面排斥,那只能使自己变得落后。

李阳的“疯狂英语”授课场面。开放的态度并不会使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交流中萎缩
2.主观抵制行不通
应该承认,从近代开始,绝大多数中国的新东西都是通过西方引进,语言也是这样。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些词都排挤出去,我们还怎么说话?新词的使用是自然而然的,主观抵制行不通。
比如说“Taxi”,大陆译为“出租车”,香港称“的士”。改革开放之初,有文章公开说不能称“出租车”为“的士”,因为香港是殖民地,我们现在再用香港的话,就是“自我次殖民地化”。但现在很多人都管乘出租车叫“打的”,“打一个的”。
后来还有一个争论:说计算机不能叫“电脑”,因为“电脑”是说机器有脑子,也就有思维,思维是和人的实践相联的,机器不可能有实践,怎么能和有思维的人脑相提并论呢?所以说用“电脑”这个词是唯心主义的,不能用“电脑”这个词,只能用“计算机”。但是现在,大概说“电脑”的人比说“计算机”的人还要多,起码不会少吧。
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习惯用港台腔的词汇。比如用“哇”、“耶”表示惊叹。过去有许多规定,不许用这样的词汇,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新一代自然而然就是这种表达方法了。现在常用的“作秀”也来自港台,是译自英语的“show”,就是表现、表演、显摆的意思,刚开始这个词也是少数时髦青年才用,现在不是也成为普通话了?我就多次在一些主流媒体上读到文章,告诫领导干部要做实事,不要“作秀”摆花架子。来自台湾的词汇还有很多,如“资讯”、“提升”、“考量”,与我们原有的“信息”、“提高”、“考虑”已开始并用。这种影响当然也不是单方面的,比如以前主要是台湾词汇单向影响内地,现在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许多内地词汇也在台湾流行,简化字在台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此我以前知道得不多。因为我一直关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港台词汇对内地的影响,但不久前几位来京的台湾学者对我说,以前内地词汇对台湾几乎没有影响,但近几年内地经济强大,内地词汇在台湾的影响也大增,并且越来越大,还举了一些例子。我记得有一个词是“氛围”,说开始他们不知道内地经常用的“氛围”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他们也常用这个词。看来由于所处环境不同,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台湾词汇对内地的影响,而他们感受更多的是内地词汇对台湾的影响。这也证明了经济发展对语言、文化取得“平等权”的重要性。这种互动,对两岸的理解、交流、统一应有正面意义吧。
前年胡锦涛总书记和连战主席举世瞩目的会谈,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双方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vision),立即被收入即将付印的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排拒来自台湾的词汇。
前面讲到“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主要是讲事实上如此,普通话是我们祖国大家庭共同的语言,大家都可以、也都有权为普通话作贡献嘛!就看谁的本事大,贡献做得多。生猛、炒鱿鱼、忽悠不是使我们的普通话更生动、更丰富嘛。当然,语言是随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发展的。总之,这种影响、互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今年2月,有200多年历史的英国《泰晤士报》在头版位置刊登教汉语的内容,这是《泰晤士报》历史上头版首次出现汉字。
3.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语言的发展,并不会导致我们传统文化精华的萎缩
在当前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语言毕竟是五光十色的,雅俗共存,鱼龙混杂。我认为无论是方言还是外语,都使我们语言更加丰富。从前日本通过中国来吸取新词汇,后来中国又大量的从日本吸取新词汇,这种师生易位就说明了想以保守、封闭的方法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结果适得其反,在许多方面更加被动。可见,想靠封闭来弘扬发展民族文化根本不可能。语言的影响力以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载体,表现更明显。
比如韩国,现在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学英语,而且政府还提供了财政支持――建了英语村,提供封闭式的学习环境。现在韩国的英语教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据说以后更是准备从一年级就开始英语教学。韩国很多家长,很早的时候就把小孩送到美国或其他英语国家去。还有更过分的,据说韩国人舌头的形状影响学英语,所以有些家长给自己孩子的舌头作手术,“整舌形”。那么韩国自己的语言文化是否就因此萎缩了呢?恰恰相反,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韩国的文化掀起了强劲的“韩流”,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更是受到“韩流”的影响。韩国的轰轰烈烈学英语和当下“韩流”的涌动,其实有种内在的联系。
大家都知道王世襄先生吧,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如家具、瓷器,甚至对鸽哨、蝈蝈笼、葫芦等都有深厚的研究。同时,他的英语也非常好。这就说明,汉语和英语并非就是对立。现在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上人们学英语的氛围热过了头,会影响、冲击汉语的使用。其实我们从近代的历史来看,众多有作为的学者都是中文功底好,又能兼通一门外语的。冯友兰、钱钟书、季羡林、周一良、闻一多、陈梦家、侯仁之……多得举不过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言,他们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但他们的外语不都很好吗?
当下在全球也出现了一股“汉语热”,当然有人不同意,认为还不热,但我认为这是相对而言的,现在学汉语的外国人比从前多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热”。在改革开放以前,我想这种汉语热是不会出现的,恰恰是我们打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别人才会来学习汉语。所以我认为国内的英语热与国外的汉语热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与韩国英语热和“韩流”的关系一样,只有开放、改革,才能增强中国的国力,中国的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才能有吸引力,中国的语言才有可能在世界广泛地使用。随着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印度一些语言对英语有明显的影响,最近有英国媒体报道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来英语也开始受到汉语的影响。
总之,只有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融入到全球的潮流中,这时候你的文化也才能对全球文化有影响,你想封闭起来,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你的文化、你的语言对外也是没有多少影响力的。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希望和大家更多探讨一些问题,谢谢!
■问答
提问:刚才您提到的若干新词,实际上都是近一百年来新产生的。我想了解一下,语言或者文字,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统,那么在新的语言形态中,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是还发生作用?是否可以说新的语言会促使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而与传统的文化毫无关系?
雷颐:我想你要问的就是新词(或者说语言)和传统文化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我觉得可以看作一个谱系。一般而言,高雅的文学性语言离传统的文化就近一点,但像政治、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词汇,往往跟传统相隔比较远,而自然科学的语言与传统最远,恐怕里面没有多少传统语言。语言的变化当然是改变传统,但也应看作是传统的发展。比如我们写文章的时候用白话文,但是如果需要还是会引用一些唐诗宋词的。
提问:刚才您提到的白话文,还有简化字等,使中国的语言从文言走向口语。但流传下来的古典诗歌散文,都是通过文言传递下来的。那么白话文是否也能像文言文一样,创造经典并流传后世?
雷颐:让我这样一个搞历史的人预测未来是很冒险的事情(笑),我就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吧。我觉得在后世那些经典的文言文当然还是依旧会流传下去。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美的东西都会被后人学习、继承、模仿。但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作为日常交流中的语言,是现在人们生活中使用的白话文,而且白话文还在不断变化。其实从清末就出现了白话报,假以时日,白话文也一定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经典。其实,已经有许多白话文学作品成为经典了。
提问:既然您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近代中国一百年来,大家都用这些新词来定义我们的文化,那中国人的身份难道只是一个国籍符号吗?它的文化内涵在什么地方?
雷颐:我觉得这个“民族身份”就看你怎么界定了。比如说按照辛亥革命以前的文化、服饰定义身份,那么我们现在就都不是中国人了,因为我们的服饰(满族的服饰)、我们的辫子都没有了。我觉得文化在变动之中,所以作为符码的“民族文化身份”也在变动之中。并不能说你背多少唐诗宋词就是中国人了,如果一百多年以前的人看我们,会认为我们从服饰、到语言已完完全全成为“洋鬼子”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认为自己还是中国人。
提问:我前一段接触了一些东南亚的华人,发现其中许多人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汉语却要重新学习。是否语言就是一个工具,相对于它背后所含的文化意义、文化身份,是次要的呢?
雷颐:我刚才讲了语言很“势利”,哪个地方的经济、文化、政治力量强,其他的人就要学哪个地方的语言,很可能以后东南亚的华人会更多地学习汉语。比如1997年以前我到过香港,香港地铁上是没有普通话报站的,而1997年以后就有了,这反映出政治对语言的影响。语言当然是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但又不只有工具的意义,语言在工具性功能外还有文化、价值意义,通过语言交流,人们能对彼此的文化、价值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提问:钱钟书先生的中文和英文水平都特别好。但是钱先生一些著作,他自己要求出版的时候要用繁体字,有的著作还是用文言写的。那么是否在传统经典文化的领域,一定要保持语言纯粹性才能研究呢?比如用英语就无法研究唐诗。
雷颐:作为学术研究来说,通过语言研究经典还是应该这样的。像刚才说的王世襄的英语非常好,但同时他又很懂传统文化,所以两者并不矛盾。所以我还是想说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学习中文或外语,常常两者都学不好:有许多人中文水平不行,而英语也同样不好。我觉得这是教育环境、体制问题,是学习的态度或方法问题。我们的国家曾经出过那么多中、英文都好的“大家”,如何借鉴他们所受教育的教育体制,是应该认真思考的。总之,不能认为要学好中文,就一定要少学甚至不学外语才好。
提问:我觉得日本对西方的研究始于中国的乾隆时期,当时日本还有专门研究荷兰的“兰学”,为什么说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早于日本呢?
雷颐:日本在近代“开国”以前,幕府曾多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兰学”确实使日本对西方科技的了解起了重要作用。但在日本被西方打开大门之前,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比兰学大得多,在日本人眼中中国依然是最强大、文化最优秀的国家,所以中国的鸦片战争对当时的日本是一个直接的刺激,从另一方面更加强了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日本大规模地引进西学,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提问:您能评价一下今天的网络语言吗?
雷颐:对网络语言我最近关注得也比较多。说实话,“网语”我看了一些,简直看不太懂。有些网络语言的使用规则和我们现在通用的口语是根本不一样的。由于对语言意思理解不一样,有时候还会引发一些矛盾冲突。有一次我看中央台的体育节目,有一个篮球队老教练在比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怒斥一个年轻记者说,你为什么写我是“骨灰级”教练,有这样骂人的吗?当时我也感觉这个记者也真是不太像话了。但那个年轻记者连连解释说这话不是骂您的,是赞扬您老的。于是那个教练更愤怒了,说“骨灰级”还不是骂人!后来我儿子对我说,“骨灰级”是电子游戏中说“资格很老”的意思,也相当于“最高级”的意思,还有对某一派最忠诚、死了烧成灰都不改变的意思,确实不是骂人的话。后来我注意到,在许多媒体中,尤其是以青少年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媒体中,早就用“骨灰级”这个词了。前年“超女”使“PK”一夜之间走红,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PK”,还是问了孩子后,才知道“PK”也是电子游戏中的“对决”。这些事使我对网络语言产生了兴趣。现在,网络语言已渗入学生的作文中了,一些中小学老师也在学网络语言,这样才能和学生交流。所以作为一种发展,网络语言已经慢慢口语化了,这是无法控制的。而且,随着“电子一代”长大成人,进入包括媒体在内的各个领域,媒体、出版物上的“网语”将越来越多,其实现在已经不少了。
现在报纸的很多文章里面都夹着外文字母了,什么卡拉OK、MP3、CDMA、DVD、GDP等等。我很赞同《现代汉语词典》的作法,把这些常用的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也作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收录进去。有人反对收,但生活中人们常用,确实已成为“现代汉语”了。人们都说:“到医院做个CT。”没有说“到医院做X射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的,如果这样说,严格要求也还不对,因为这“X”也不行,也是西文字母。大家都说到KTV唱歌去,不说到“机内预先录制无人乐队伴奏音响设备包房唱歌去”。看懂“DNA”的人比看懂“脱氧核糖核酸”的人要多得多吧;现在“全民皆股”,做股票的人天天要看“K线”,等等,这类事太多太多,也只会越来越多。“现汉”确实已无法将这类词汇排除在外。
中国传统文字是竖写的,那种把横写的文字讥笑为“蟹行文”,把曲溜拐弯的字母文叫“蝌蚪文”,而我们现在的文字早就“蟹行”了,如今连许多报刊的文章中都加有“蝌蚪文”了,而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后词汇的变化更难预料。
结束语
感谢雷颐先生刚才精彩的演讲。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语言,语言的许多变化、发展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可能很少察觉。雷颐先生的演讲给大家一些启发,让我们跳出生活的圈子,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语言,认识到语言对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让我们再次感谢雷颐先生。
|
●博谈杂议 2007年第5期 《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及现代价值 号称“武经冠冕”的《孙子兵法》,其价值早已超出了兵法的范畴。前些年国外企业界兴起的“孙子兵法热”就是明证。不过这本书的本质仍是军事思想。过去我曾专门研读这部书,这次有幸从光明讲坛上拜读吴如嵩将军的演讲稿,许多问题豁然开朗。 我觉得,学习兵法,首先一条,应如清末四川盐茶道赵藩题武候祠联语所言:“从古知兵非好战”。学兵法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打仗,而是赢得和平。这个观点,我想应该符合孙子的思想。关于这点,有必要全面认识战争的形式――战争未必就是兵戎相见、刀光剑影。通过舆论、外交手段挫败敌方战略企图,同样是战争的表现形式。 作为一部产生于冷兵器时代的军事著作,在今天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如何实现其成功转型,使之继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吴将军在谈到《孙子兵法》应对新形势的考验时指出,成功的转型需要的是“化西”,而不是“西化”。我以为,这一观点实际上强调的是“固守己本”,是“把根留住”。我想,吴将军就如何对待传统兵法的原则性意见,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待祖国其他传统文化成果。 江西赣州章贡区委 陈相飞 作为一名军校大学生,看了吴如嵩将军的《〈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及现代价值》以后,我有格外多的感慨,也很受启发。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深厚,逻辑缜密严谨,体现了我们东方文化的一种大智慧。从古至今,历代的军事家、兵学家无不从《孙子兵法》中汲取营养和智慧,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而且许多国外战略家也同样深深地陶醉于这部中国传统战略著作。如今《孙子兵法》早已不再是简单意义上单纯的战争著作,孙子的思想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体育、领导艺术、人事管理、人生追求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人们在从古人深邃的思想中获得启迪的同时,也丰富了《孙子兵法》的内涵并为其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如果我们能对《孙子兵法》进行细细地咀嚼和品味,就不难发现,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孙子兵法》中慎战备战、倡导和平的人文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尤其值得大力高扬。 与此同时,当前市面上关于《孙子兵法》的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质量良莠不齐。许多假冒伪劣产品都充斥其中。还有一些人打着“孙子兵法研究专家”的旗号四处挂牌讲课,狭隘地理解《孙子兵法》,并将其与一些生活上、官场上的琐碎之事联系起来,将《孙子兵法》低俗化应用,把这部兵学圣典搞得庸俗不堪。我希望更多的像吴如嵩将军这样的专家和学者能多推出《孙子兵法》研究方面的精品,为国人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孙子兵法》的文化氛围。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李祥辉
南京解放军理工大学 李冀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