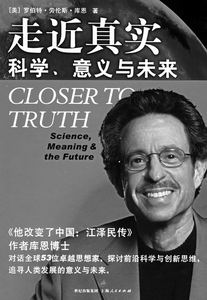 亚历山大・凯普伦:南加州大学法律和医学教授,南加州大学研究健康政策与道德伦理的太平洋研究中心的合作理事。前任美国生物医学伦理顾问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凯普伦:南加州大学法律和医学教授,南加州大学研究健康政策与道德伦理的太平洋研究中心的合作理事。前任美国生物医学伦理顾问委员会主席。
安德里亚・科瓦克斯:南加州大学柯克医学院小儿科与病理学副教授。
罗伯特・坦普尔:美国国家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药品评估与研究中心医药政策部副主任。
库恩:让我们来描述一下临床实验的主要特点吧。
坦普尔:最简单的临床测试是给病人进行测试性质的治疗,对一个随机的群体使用你感兴趣的药物,和对另一个类似的随机的群体使用你感兴趣的药物,和对另一个类似的随机的群体使用安慰剂(指那些表面看起来相同,实际上不含任何药物成分的惰性物质)
剀普伦:研究通常被设计成我们所谓的“盲法”实验,这意味着被测试人和测试者都不知道谁会得到积极的治疗,谁会得到安慰剂。试验被充分地伪装以至于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况。
库恩:如果只有病人不知道,而研究人员知道谁会得到积极的治疗而谁不会,这叫做“单盲试验”,只有双方都不知道才叫做“双盲试验”。临床试验的黄金准测是执行“双盲”原则。
库恩:什么是临床试验的阶段性?
坦普尔:第一阶段试验是指首次将某种药物介绍给人类;这些药物已经在动物身上做过研究并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效果。现在你将这种药物用于小范围的人群,有时是正常人,有时是病人;一般来说直到受药者出现了某种副作用,如恶心,头晕或者类似的反应,你的剂量才会停下来,这说明多大的剂量是人体能够忍受的。主要目的是要确认药物的可耐受性及安全性而非治疗效力,进而确认可忍受的安全剂量范围。第二阶段试验是对药物的首次控制性试验,通过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严格挑选的人群内进行的。这时,研究人员希望得到结果,看药物是否具备他们所期望的效果;例如,在艾滋病药物的试验中研究人员可能会比较两种不同的药物的效果,这两种药物的组成物、剂量和/或者服药时间不同,通过监控每单位血液里的病毒粒子来判断药物对艾滋病病毒的效果,提供有关药物是否有效力及剂量与效力关系的初步讯息。第三阶段试验是更广泛的控制性测试,更准确地控制测试,观察不同严重程度的疾病对药物的反应、不同的受测试人群(如男性和女性、黑种人和白种人、老年人与年轻人),总之是更广泛的试验,因而可以了解药物的更多副作用。毕竟,如果说在第二阶段有200人参与,那么你无法知道一旦发生在500人的范围内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如果你进入第三阶段有数千人参与,那么你至少可以发现副作用发生的千分率。
库恩:为什么媒体对新药的临床试验有如此多的指责?
凯普伦:有一些非常糟糕的临床试验。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199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针对一个18岁的年轻人作了基因治疗试验,结果年轻人死了。年轻人得了一种罕见的肝脏疾病(这种疾病经常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治疗手段是将健康的基因植入他的肝脏中,这被认为是风险非常小的。虽然年轻人并不符合参与的标准,但他还是参加了。他变得非常虚弱,四天后他去世了。他的父亲说儿子是自愿帮助其他的患者而参与试验的。
库恩:使问题变得棘手的是年轻人的症状本来比较轻,如果得到很好的控制,肯定不会有生命危险。
凯普伦:是的,他的病情并不是很严重。以下是大家的议论:如果被试验的对象病情非常严重,例如婴儿,明显地无法自己作出同意参加试验的决定,但是因为他们病情已经危急,如果试验有效,对病人而言是极大的帮助,从伦理上人们是能够接受的;然而这名自愿参加试验的年轻人病情并不是很严重,而且饿不会受益于这个试验,他没有一点私心。另外一个议论的话题是研究人员以及整个研究事业与企业利益相结合的程度。实际上研究人员和大学对那项技术的发展是有所投入的。
库恩:所以说大学和研究人员在这个过程中是经济利益的?这会将一个不辛的情形转变成一个丑陋的情形。
凯普伦:调查人是公司的主要所有者,他发起这项研究,大学在其间是有经济利益的。如果研究成功,双方都会成为经济利益的受益者。
坦普尔:谁最支持临床试验?制药公司,显然他们是收益相关者。但有时他们的利益不见得很清楚。他们确实想发现某种药物是否会伤害人,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将有可怕的副作用的药物推向市场,这对他们而言也是灾难,所以封闭坏消息并不是他们的目的。然而,制药公司的动机是复杂的。最通常的测试新药物的方法就是一家制药公司,作为明显的利益相关者,花钱请独立的调查人来从事试验。按道理,调查人是真正独立的,意味着他/她对于试验的结果没有利益关系,他/她会高质量地开展调查,严格地监控试验以确保试验按照最高标准实行。这是通常的模式。
库恩:另外一个伦理方面的关注焦点在于,临床试验是由发达国家的制药公司在第三世界实行的。当特定的临床试验还没有被联合国同意时,因文化的不同,问题会变得非常敏感。
凯普伦: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某个制药或者医学设备公司想为美国市场生产某种产品,但是不能在美国做试验,因为已有的医疗是有效的而且确定的。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去一个还没有针对某种疾病进行治疗的其他国家,拿我们的新药与安慰剂做比较。”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的反应既有可能是对即将到来的治疗感到迷惑,也有可能是某个政府官员承诺了什么或者私底下拿了红包。
坦普尔:然而,接受临床试验的第三世界的人们因此而获得的医疗条件可能会比不接受要好得多,特别是那些得到积极治疗的人们。
凯普伦:当然。人们可能认为接受这种临床试验后他们的经济状况会好些,然而试验可能受到严格的人数限制和时间限制,而实验的产品可能并不适合他们,即便适合他们,他们也花费不起。有人感到难以接受就抗议不应该允许制药公司进行此类研究,这在伦理道德上是错误的,国家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甚至不应该接受这样的数据。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一个国家面临一种严重的疾病,因费用昂贵需要得到第一世界帮助时,第一世界的反应就是授权自己的科学家与其他地方的科学家一起来研究替代性药物,成本大概是原药物的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第三世界的官员从一开始就知道便宜的药物的疗效明显不如那种昂贵的药,但是因为他们无法提供其他选择,那种便宜的药物便会显得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受欢迎。
科瓦克斯:一个特别的例子是某种防止围产期艾滋病毒感染的药物在南非和泰国的临床测试,这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我们应该保持美国的标准,给孕妇和刚出生六星期的新生儿服用AZT(艾滋病防护药),但由于成本过高,这种药无法在撒哈拉非洲地区和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实行。所以一个低剂量的AZT试验与安慰剂试验同时对母婴实行。
库恩:这是一个伦理悖论。比如,你知道有一种已被试验的药物能将艾滋病病毒的传染率减少到三分之二,然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你却用一种改良药物的方式在进行临床试验,而一开始你就知道它的效果明显要差一些。
科瓦克斯:但是他们无法支付起第一世界国家水平的医疗费,他们也不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治疗体系。
库恩:这是一个伦理学难题:你之所以有意地实施低标准的医疗,只因为那是惟一能供应得起和能够执行的方式?你实行安慰剂控制难道不会从根本上拒绝那些真正急需有效的治疗从而得以生存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婴儿吗?
科瓦克斯:完全是这样。
坦普尔: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你不能拒绝对病人实施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再实施无效治疗了。批评家们说在这一点上惟一可以接受的试验是比较低剂量的AZT试验与复杂的美国标准的医疗的区别。
库恩:哪些治疗是昂贵而复杂从而无法在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
坦普尔:这些国家需要回答的问题并非低剂量的、短期的AZT治疗是否与更大剂量的、长期的美国标准的治疗同样有效,而是低剂量的、短期的AZT治疗是否有效果。它并不一定要和美国标准一样有效,可能只有一半的效果,但是如果它确有效果,那些国家需要迅速知道它,因为这样的治疗是可行的而且能够使情况大为改善。
凯普伦:这里是假设是第一世界国家的药物将不被利用,而你正在试验的药物可能是可行的,而且有某种承诺使得它必须是可行的。我想实施试验的制药公司本应该对提高被帮助的国家的科学和伦理水平做出一定的贡献,所以他们会留下一些积极的东西给第三世界国家,而不仅仅是用他们的人口来做试验。如果你没有某种符合伦理道德的假定和药方以及具体的要求,那么你会为错误的行为打开方便之门,那可真是一件糟糕的事。
库恩:例如什么?
凯普伦:穷人会签字同意做任何事情;动机则既有可能是对治疗方案的误解,也有可能纯粹只是为了一点点钱或者两者兼有,那么他们差不多就是天竺鼠了。我不认为这是大多数美国公司想干的事,但是诱惑的确存在。真实的科学和伦理评价应该既被制药公司所在的第一世界需要,也被临床试验的对象――第三世界所需要。
坦普尔:许多制药公司正在事实抗抑郁剂、抗组胺剂和其他类似的试验,正如他们在美国所从事的那样,这些试验正在东欧和南非洲进行。制药公司可能想在那些国家推销他们的药物,但是他们的愿望不可能马上实现,因为这些国家大概只会使用相同药物的普通版,他们不会花钱买原药。
 库恩:更穷的人就像天竺鼠一样吗?
库恩:更穷的人就像天竺鼠一样吗?
坦普尔:我们也对美国公民做同样的试验,就像天竺鼠那样。同样的抗抑郁剂试验在美国、西欧、东欧和拉美都进行。
库恩:虽然这样,但是仍然有不同之处。如果临床试验是在美国实施,如果治疗有效,至少参与临床试验的人们将受益于它的一般性使用。而在非洲则完全不同。
坦普尔:也许是这样。然而我们也必须知道,作为在这些更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临床试验的结果,制药企业留下了能够继续试验的基础设施,也许还留下了适用于医院的建筑。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学习到如何诊断病情以及其他方法、手段和设施,否则的话,他们无法了解。
库恩:所以这里有一个总结性的问题:第一世界的制药公司利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优势,或者说他们为这些穷国的人们提供了某种他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好处?
凯普伦:你可以就两个方面发表意见,但是收受财物来允许临床试验在他们国家实施,这毕竟是不适当的诱导。
科瓦克斯:我认为外国的、第一世界的制药企业和保健企业以任何方式参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卫生保健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当地的影响力。
坦普尔:制药公司有合适的技巧和资源。
科瓦克斯:只要医生不卷入其中、在剥削人们之后溜走就行。
凯普伦:那一定是最糟糕的事情。
科瓦克斯:你教育人们,你培训当地组织,你带来资源;然后你告诉他们如果开展试验。
凯普伦:但是有时候你培训和服务的人员已经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是科学家、医生和其他将接触那些奇异的设备和建筑的人;是的,你可能会私下里帮助人们使他们的生活更富裕,但是他们同意以个人身份参与临床试验,以及承担各种参与的风险。他们不一定要报偿,并且对整个社会有益。另一方面,有时制药企业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有益于整个社会的。
科瓦克斯:我们正在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例如对艾滋病的治疗。现在我们将开始研究其他疾病如肺结核和疟病――我们将研究环境、水、每一件东西――我们将给予那些深受疾病困扰的人以难以置信的积极影响。
坦普尔:批评家们曾经善意地抱怨、我们这些科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那些疾病时,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似乎并不那么迫切。
凯普伦:因为那不是我们国家的疾病。
坦普尔:对,因为其间并没有大量的钱财。所以我相信当这些大制药公司深入发展中国家来做临床试验时,从总的效果来看是有益的。
罗伯特・库恩的结束语
临床试验的伦理学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我们追求集体的利益,但是我们也尊重彼此的人权。我们冒险来发现新的治疗方式,但是我们不能为了加快治疗而失去人性。
道德理想,平行处方,结合了病人的承诺和调查人的积极监控的数据。当人类的生命危在旦夕,我们能做出富有同情心的妥协――无需操纵临床试验,也不需要达到某种最适宜的数据。
我们如何能够加速将有价值的药物推向市场的人性化过程?最有前途的是通过超型计算机的模似对药物所做的“干试验”,这是一门叫做计算机生物学的新学科。用硅片来做实验就不存在论理学问题了。
(摘自《走向真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定价:3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