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之地。这里,曾经聚集着一大批对中国文坛有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作为人文社的一名编辑,王培元用他自己的视角,与多位前辈的魂灵相遇,感受新中国文学的风雨历程……
牛汉:“汗血诗人”
1953年3月,牛汉从部队转业,进入人文社现代部,在冯雪峰领导下工作,曾先后担任过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著)、《上海的早晨》(周而复著)、《山乡巨变》(周立波著)和《艾青诗选》、《十月的歌》(陈辉著)等书的责任编辑。1955年5月,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他第一个遭到拘捕。
直至1957年5月,他被释放回家,交给街道派出所看管。8月20日,公安部把他定为“胡风分子”。接着,社里召开党支部会议,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牛汉在会上,听完宣布,只大声说了七个字:“牺牲个人完成党。”
冯雪峰和王任叔也参加了会议,但他们始终缄默,一言未发。
1957年8月14日,社长王任叔让他下午到中国文联礼堂,参加批判冯雪峰的会。他到场时,会场已坐满了人。他找了个位子坐下来,低着头,等着开会。在熙攘嘈杂的纷乱中,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低着头,不想答应。

可那喊声很大,仍在“牛汉――牛汉――”地叫。
他只好抬起头,循着声音望过去,哦,原来是艾青!
艾青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直盯着他,问:“是牛汉吗?”
他点了点头。
艾青提高了声音,关切地问:“你的事情完了吗?”
他回答:“没有完,算告一段落了。”
旁边好多双眼睛,惊异地审视着这两个有“问题”的诗人。
想不到,正在承受着政治批判的巨大压力的艾青,竟然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又大又亮,不是朝着牛汉,而是面向众人,几乎是用一种控诉的语调,大声说:
“你的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
接着,他以朗诵诗的那种拖腔,高声地喊道:
“时――间――开――始――了!”
谁都知道,这是胡风的一首著名的诗的题目。《时间开始了》出版时,是艾青亲自为胡风的这本诗集设计的封面。
“文革”一开始,牛汉即被关进“牛棚”。“干校”的军代表看他人高马大,就让他干拉车运输等最繁重、最疲累的劳役,像牛马一样使唤他。
两三年之后,管制放松了,活儿也不那么累了。他成天幽灵般地游荡在“干校”附近日渐空茫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难,反刍人生。诗,突然从心中苏醒了。他有了写诗的冲动。他这才感知,一个诗的世界,封存在、冷冻在自己的心里,实在是太久了。
牛汉说:“面对着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正是扇动着的翅膀。”
后来,他一个人住一间屋,取名“汗血斋”,在杂记本上草草地记下了几十首诗。在最没有诗意的日子,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诗如钟锤一样敲醒了他,提醒了他,他又开始写诗。就在这“汗血斋”里,诞生了他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诗篇。
1974年底,他终于获准回京,先在出版社的资料室抄了两年卡片。1978年参加《新文学史料》的筹备工作,1983年起一直担任这份在“新时期”文坛有很大影响的大型杂志的主编。
那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新文学史料》刊发的若干文章,涉及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事件或者话题,有时便会感到来自上边的压力,甚至说这是“雪峰派”、“胡风派”的杂志。
有一次,上面还专门派了一个“调研员”,到社里对《新文学史料》审查了两天,想把这个杂志停掉。不久,一个社领导找牛汉谈话,说《新文学史料》“有方向性的问题”。牛汉毫不含糊,针锋相对地说:“你具体说说,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个领导支支吾吾,又说不出来。
有一阵儿,连社长韦君宜都觉得有些为难了,不想继续办《新文学史料》。她对牛汉委婉地说:“牛汉啊,可能上边觉得办起来太困难了、太复杂了一点,咱们是不是停了吧?”
牛汉理直气壮地质问道:“《新文学史料》有什么错?大部分作家,包括丁玲、艾青都很支持,很欢迎,为什么要停?”
事后,韦君宜对他歉疚地说:“牛汉啊,这不是我的意思,不是社里的意思,是上边的意思,我这个人太软弱,我也没有办法!”
没有牛汉几次顶住压力,没有他的“毫不含糊”的倔脾气,很可能《新文学史料》早就夭折了。后来,韦君宜告诉他:“胡乔木说过,拿牛汉这个人没有办法。”
牛汉是一位用生命拥抱生活、拥抱诗的诗人。他说过,“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同体共生”。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对于牛汉来讲,再也恰当不过了。
有一次,艾青问他:“牛汉,你说,你这许多年的最大的能耐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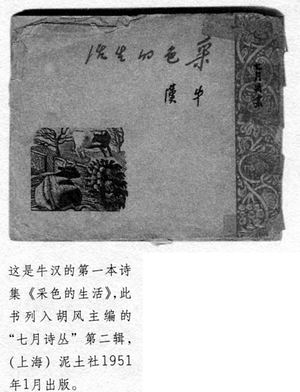 牛汉不假思索地回答:“能承受灾难和痛苦,并且在灾难和痛苦中做着遥远的美梦。”
牛汉不假思索地回答:“能承受灾难和痛苦,并且在灾难和痛苦中做着遥远的美梦。”
艾青知道牛汉的性格一向是很躁动的,他不止一次地提醒牛汉:“做人做诗要再朴素再深沉些。”
牛汉曾经为加拿大一位女诗人安妮・埃拜尔的这样一行诗流下热泪:“我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有美丽的骨头。”他说:“我的骨头不仅美丽,而且很高尚”;“我的骨头负担着压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难的重量”。甚至把骨头和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称为自己的“感觉器官”,“它们十分敏感而智慧,都有着异常坚定不泯的记忆”;“我只能用伤疤的敏感去感觉世界”,“没有伤疤和痛苦也就没有我的诗”。他还企望,自己和诗总是不歇地向梦游中看见的美妙远景奔跑,“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
一个曾是他的诗友的著名政治抒情诗人对他说:“牛汉,你的诗里的‘我’,是‘小我’,我的诗里的‘我’,是‘大我’。”牛汉对他说:“你的‘大我’空空洞洞。我的‘小我’是有血有肉的。”
这,就是诗人牛汉,诗里蒸腾着“汗血气”、被称为“汗血诗人”的牛汉!
牛汉的确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个性鲜明,脾气倔强,极有血性。
1965年11月26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位于天安门南侧旧棋盘街)审判胡风的大会上,他敢于公开为胡风辩诬。这次审判,通知他和绿原、徐放、谢韬、阎望、芦甸等人,出庭作胡风“反革命罪行”的“见证人”。事前,高检院的一个女干部专门找他谈话,和他打招呼,让他实事求是地揭发、检举胡风,分给他的题目是“胡风是怎样把我拉下水的”。
在法院的接待室里,他见到了绿原等几位友人,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各自呆坐着,等候被传唤出庭“作证”。轮到牛汉了,他本来应当照着经过审定的发言稿讲,可到了最后,他又说道:“1953年9月,胡风攻击党的领导,说他们对文艺界的几位领导偏听偏信,这是胡风惟一一次攻击党的言词。”
主审者大声质问道:“是惟一的一次吗?”他回答:“我只听到这一次。”主审者喝令他停止发言,并立即退出法庭。
牛汉又是一个脾气很执拗的人。
丁玲创办、他担任执行主编的大型文学杂志《中国》,被作协某些领导强行停刊以后,一个作协的头头见到牛汉,振振有词地说,此事他也是不得已。牛汉当即气不打一处来,说:“我不谅解!我不谅解!”当时,主持作协工作的是党组书记唐达成,牛汉虽然也认为唐“人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中国》停刊问题上,他表示对唐“不能原谅,我永远不会原谅”。
1999年人文社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在一次初选会上,我发言说自己作“知青”时,读过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和《向困难进军》,印象很深。牛汉马上接着说道:
“说老实话,我不喜欢!他写这些诗的时候,我们正在受难!”
他总是这样,在表达意见和看法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直来直去,态度鲜明,听者也觉得爽利、痛快。他绝不像我们这样活得窝窝囊囊、唯唯诺诺、怯懦卑微,说话先要瞧着别人的脸色,想着对方喜不喜欢听,听了舒服不舒服,总想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地把话说得圆融、圆通、圆滑。
严文井:“我没有自己的思想”
1951年春严文井奉命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由于他不擅长起草红头文件,从1952年年底起就调离了中宣部,去筹建作协。他先后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务。1961年又以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人文社社长、总编辑职务。几乎文艺界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严酷的政治运动,他都是参与者、目击者和见证者。

1996年6月9日,严文井看望冰心。
作为一个作家,由于他长期置身于作协的权力中心,不得不遵命写一些“大批判文章”(比如,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进行“再批判”时,他写过《罗烽的“短剑”指向哪里?》),后来又写了大量的”思想汇报”、“自我检查”、“交代材料”,“文革”结束时“还保留了足足一木箱”。
所以,回首过去的时候,他说自己“时常做一些蠢事”,“做过荒唐的事情,错误的事情”。
但他并不是那种在权力中心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人。他从不趋炎附势,主动整人。做表态性批判发言时,也从未疾言厉色。在一次批斗丁玲的会上,别人的发言都是政治性批判,言辞激烈,火药味浓得很。轮到他发言了,却突然冒出一句“陈明配不上丁玲”来,引来哄堂大笑。
对于“左”的祸害和遗毒,严文井有着椎心刺骨、痛彻肺腑的经历与感受。他也曾经“左”过,在“左”的潮流中,亦不免随波逐澜。他的胞弟,当年跟随他一起奔赴延安,在“抢救”运动中被无端地怀疑为“国民党特务”,交给了在“鲁艺”教书的长兄来“教育”、“挽救”。严文井对不肯违心承认自己是“特务”的胞弟说:“党有党纪,家有家法”,还挥起了拳头来教训他。之后,他的胞弟被逼自杀,所幸未死,但落下了精神疾患。严文井为此而痛悔终生、罪疚终生。
“神话时代已经结束”,从漫长噩梦中终于醒来的严文井说,“我们可以不再向老龙磕头了”。还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几乎是一个怀疑派;经过了漫长的不怀疑的岁月之后,我重又感到‘怀疑’的一定价值,我把‘怀疑’当做认真分辨和深入思考的同义语”。他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一个一个疑问相继得到解答”。
 |
|
严文井自画像 |
他说,“我听了一辈子训斥”,“我的过失已经不可挽回”,希望读者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出这些悔恨,代他弥补。
他还画了一幅自画像《严文井自剖》,郑重地钤上了自己的印章,复印了好多张,分赠给同事和朋友。这幅自画像意味深长,嘴和脸都扭曲了,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心灵的影像,也是他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肖像。
1973年,严文井从“干校”返回北京;担任人文社临时党委书记,重新主持工作。在极左思潮仍甚嚣尘上的严峻局势下,他和韦君宜率领全社员工,在异常艰难中,克服重重阻力,逐渐恢复了编辑出版业务。
有一回,他当面对担任作协领导职务的人说:“很多我们当年犯过的错误,他们还在犯!”说者痛心,听者亦不免有些惊心。
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几十年之后,他对人,对人性,对人生的虚妄,对人的局限性和悲剧性,对政治,对历史,对政治的凶险,对历史的荒诞,认识得更深刻了、更透彻了。
他似乎获得了一种心智的澄明,有了一种大彻大悟,但又依然有深深的惶惑。他的幽默里,就有这惶惑在。
他写过一个年轻人,“他渴望美,却看见了丑,只有从丑恶与丑恶之间的缝隙中看到一些美。他感到困惑”。我觉得他写的,也是他自己。
五十年代初严文井进京后,在被称为“大酱缸”的东总布胡同46号作协宿舍,住了很长时间。几番雨打风吹,他看到一些“高级作家”荣升当官了,一些“机灵人”“弄巧成巧”或弄巧成拙地离开了,一些作家被放逐了,一些作家死去了。他了解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他熟悉那些风云人物,但没有写过他们,却怀着柔和的心,描写了从山西山沟沟里走出来,住进这里以后并不自在的“乡巴佬”作家赵树理。
他写了这位早已在全国大名鼎鼎的“土头土脑的老赵”,由于儿子没能分到上重点小学“育才小学”的名额而自打耳光、放声哭泣的自我发泄;写了与一般都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的可以称之为“洋”的有来历的“官儿们”相比,“老赵”在“大酱缸”里算不上个老几的“二等公民”的地位。
这些发生在著名乡土作家赵树理身上的小故事,与时代的潮流相比,既不浪漫,也没有诗意,太鸡毛蒜皮、不值一提了。然而,它的真实性和严酷性,是令人战栗的。严文井就是这样,把某些被宏大历史叙事无意忽略或遮蔽了的真相,不动声色地赤裸裸地揭示给了我们。
读了《赵树理在北京的胡同里》,先是略感意外,继而深长叹息,心酸不止。
去年的一天,和牛汉先生谈起严文井。他说:“新时期以来,严文井可以说是大彻大悟。1980年《新文学史料》发了《从文自传》,那会儿有些人对沈从文还有偏见。楼适夷就大不以为然,说‘我是《史料》顾问,为什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哪?’严文井给我打来电话说,‘发得好!’1989年周扬去世后,我到八宝山参加了追悼会,消息第二天见报了,严文井看到后给我打电话,说,‘牛汉,你不应该去。周扬这个人,不可信。’我就对他说,‘他不是忏悔了吗?不是当众流过泪吗?’严文井说,‘他在延安就这样,善于表演,今天对你流泪,明天就可能整你。’”
他是曾经想好好写写周扬的,据说,甚至已经开了这样一个头:“我怕你,我讨过你的好,但我不算你喜欢的前列干部,因为我是一个笨蛋……”但是,他又觉得,要写就不能含糊,得按照自己的看法、想法来写,但这样就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
后来,在一篇题为《心债》(1997年8月底)的文章里,严文井提到,他欠周扬一篇文章,没有“公正地”既说说他的“好话”,也说说他的“缺点”。
权力左右的局势为十年。
智慧和机灵左右局势约为百年。
被真理左右的局势是永恒的,无论看起来是怎样变幻不定。
――他曾在笔记里写下了这样的看法。但又觉得,现实“难于把握”,“我的现实观也许是荒诞的”。他说自己“是乐观的”,是一种“悲观里的乐观”。
虽然离休以后,他赋闲在家,深居简出,但头脑从未停止过思考。他的思考既是深刻的,又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超越性。有一次,他和来访的陈四益聊着聊着,突然激动起来,声音也提高了几度,大声说:
“人家总以为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也自以为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但是,细想起来,我算有思想吗?我真的有自己的思想吗?没有,我没有自己的思想。”
(摘自《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