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
初试译笔
儿童和少年时代,我记忆中的哈尔滨是一座有异国情调的、又充满诗情画意的、畸形的城市。道里、南岗和马家沟是半
我于1926年出生,1933年进入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的教会学校,读了十年书。同学多来自不同的民族,有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朝鲜人、中国人等等,以俄罗斯人居多。大家通用的语言是俄语。老师主要是俄侨,用俄语讲课。
我的学习成绩平平。放学回家常常痛哭,因为听不懂老师的话。经过几年的磨炼才慢慢熟悉了俄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与艺术。
老师的作用不可低估。那时,语文课讲授的就是俄罗斯19世纪作品。作品中充满对奴隶制的反抗,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弱者的关爱,对民主的向往,对美的追求。语文老师授课时,总是声情并茂,她把小说中的情节讲得活灵活现,如同她亲身经历。我们被老师那带磁性的声音深深地感染着。
我们的教务主任格雷佐夫(笔名阿恰伊尔)是当地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发起组织的“丘拉耶夫卡”文学会,在俄罗斯侨民当中颇有影响。文学会团结了一批文学爱好者,组织各种活动,地点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有的语文老师就是那个文学会的成员。
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俄罗斯文学艺术拷问人生的重大课题,但小说中的故事、诗歌中的音乐旋律、绘画中的感人场面,却把我带进一个梦幻的世界。
与外国同学们交往、聊天、拌嘴,用的都是俄语。俄语成了我母语之外最常用的语言。俄语沟通了我和外国孩子们的关系,促进了相互理解与彼此信任。从小我就感受到语言的力量。长大以后,我期盼的就是民族之间的友好与和睦,就是从事与俄罗斯文学艺术有关的专业。
我在学校即将毕业时,由于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便试着进行翻译。我译的第一篇作品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
当时我的俄文水平不高,我的汉文只限于生活用语。我哪来那么大胆子?虽然是一篇小文章,但毕竟是经典名篇。现在想起来真是汗颜。
我反复地读原文,从字面上理解了散文诗的内容,便用自己仅知的词汇开始翻译,然后把译稿寄给了当地的《大北新报》,用的笔名是“雪客”,是对迷恋雪的寄情。没有想到,过了不久我的译文居然见报了。那是1943年,我十七岁。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伸手触到了顶棚――我家住的是个小平房,比较矮。
我以为发表一篇作品并不难。这事刺激我继续翻译了几篇,有的发表了,有的则石沉大海。
哈尔滨是我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我有幸在1946年便认识了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和身穿布衣的东北民主联军战士进驻哈尔滨市,给这个洋气十足的城市带来了山沟里的自由清风。我忘不了街头上敲锣打鼓扭秧歌的欢腾场面和震荡长空的喜悦歌声,更忘不了老革命们对我的教诲。那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我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中苏友好协会当时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除致力于巩固中苏两国关系之外,还团结、教育、改造深受奴化毒害的青年,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在友协领导下有报刊、书店、影院和各种文艺活动组织。工作不分你我,大家都争着干,无所谓上下班制度,办公室就是寝室。翻译、写作、绘画、编刊物、布置会场、画广告、管理图书……只要工作需要,我就高兴地去完成。
友协的合唱团要演唱新的歌曲,于是我便着手翻译苏联流行歌曲的歌词。我前前后后译过大约几十首。译后交给来自延安的刘炽、瞿维等音乐家们配乐。他们开始直皱眉头,告诉我歌词不能随意翻译,否则很难配曲。在他们指导下我才明白,翻译歌词必须把每行歌词分成音节,并按音节译出原文;还必须把译文中的重音安排在原来的重音词的音节上,否则词与曲要表达的感情就不一致了。如果当时学一学诗学,学一学音乐,也许不会盲目地或机械地翻译,可惜我没有用心去钻研,翻译只停留在实践阶段上。有的歌经过他们配乐之后,曾流传一时。
1947年我译了《保尔 ・柯察金》,它是根据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剧本中的主人公保尔深深感动了我,因为在那之前,我还没有见过那么坚强、那么忠贞、那么勇敢的人。在我翻译之前还没有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剧本中全是对话,我觉得翻译剧本似乎比较容易些。
三年以后,我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观看这部话剧时,发现对话中有些东北土语,相当刺耳。那时我才理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艺术,不是每句话都可以印在书上或搬上舞台的。
1948年,我译了冈察尔的短篇小说《永不掉队》。这是对自己汉文的又一次考验,同时也是对生活的一次考验。
我从小说中理解到:人的一生应当永远向前,不可停止,更不能后退。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篇译文曾一度被选入语文课本。三十年后的1978年,我将后来译的冈察尔其他短篇小说和《永不掉队》合编成一本集子。有一位朋友读后,说了一句话:“你的文字三十年来没有进步。”这好比给我当头一棒,使我警觉起来,我开始检查自己的译文,认识到朋友的话是中肯的。从此我认认真真地学习名家们的译著,学习他们的文字、他们的翻译技巧。
多少年后,我翻译的作品多了些,积累了一点经验,知道从事文学翻译不仅要精通作品原文,理解它所表现的思想、它所反映的生活和文化内涵,而且还需要很好地掌握母语,要学会转化,又要善于创作。文学翻译像是带着枷锁跳舞,在受到原文限制的情况下,仍然要展示出舞蹈的美姿。到了晚年,甚至有些不敢动笔,总觉得对原文没有吃透,用汉文表达不尽原意。
1954年,我从东北中苏友好协会(沈阳)调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络部当一名工作人员,大部分时间是接待苏联代表团,或陪同我国代表团出国当口头翻译。
口译――我的大学
口头翻译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它本身需要译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大量的语汇、良好的记忆力、转化时的敏感等等。我在这些方面都有缺陷。
少年时代接触的汉文语言不纯,历史又被篡改阉割,道德理念异化,心灵所受的摧残是难以形容的。走进社会,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本身带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时某些看法也没有明确观点。比如,我曾对口译有过困惑,是戈宝权先生给我解开了这个疙瘩――1949年他去苏联经过哈尔滨时,召集从事俄文翻译工作的人开会。那时,他针对我的困惑推心置腹地讲了一段话。他说:关键是译什么和为什么人而译。话很简单,我顿悟过来,从那以后我明白翻译的意义,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路。
口译中我有很多失败与教训。
记得有一次中苏两国作家相聚,在餐桌上一位俄罗斯女诗人敬酒,激动地讲了一段话,然后用俄文朗诵了一首中国古诗。敬酒辞,我翻译了出来,可是那首诗怎么也译不成,只好译了个大概意思,主人们还是不知所云,感到很失望。我也感到无地自容。
又有一次我国代表团出访苏联,两位科学家对话时,主人讲了一段话,我不懂,反复问了两遍,还是没弄懂。我只好按大意译了。我方代表表示怀疑:“不可能吧?”弄得我只好承认自己在这个领域无知。
还有一次是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席间谈到双方办刊物事宜。总理说对方刊物的读者有从事俄文的专业人员、大学教授、文化工作者、大学生和职员。我译时,把职员忘掉了。周总理立刻意识到了,说:“你译错了!”我一时愣住。席间苏方有多位著名汉学家,他们也一怔。周总理说:“我提到五种人,可是你译时停了四顿,显然落掉一种读者。”周总理真是英明。
当然,口译中不止这些教训,但这些教训足以督促我补课再补课。学古文、学科学,学各方面的知识;锻炼自己的记忆力。那时我每天早晨一起床首先是朗诵俄文,训练讲话能力;每天在特备的纸条上记上几十个单词,只要有空闲时间就背诵;每天看见报上出现新词汇,我便找出俄文译法……那时,年轻、精力旺,但也没有少下工夫。我知道勤能补拙,笨鸟先飞。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与俄罗斯的情缘越来越深了。
我担任口头翻译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一些苏联文艺界人士,听他们谈文学,听他们朗诵,很受启示。我意识到语气与音色的重要。
记得1959年,苏联著名诗人吉洪诺夫在武汉大学向广大同学朗诵他写的关于中国的诗。那天,他身体欠佳,说话有些吃力,但当他走向麦克风开始朗诵时,俨然变了一个人。他的脸上立刻泛起了红润,声音越来越洪亮,眼睛闪耀着光芒。有时他挥动一下手臂,借以加强诗句的力量。他的朗诵激发了我国大学生的热情,掌声、欢呼声震得地板都在抖动。我也尽自己的努力在译,但达到同样的效果太难了。好在吉洪诺夫的字句清晰明了,译成汉文易于接近原文。
我国改革开放时,我和戈宝权应邀去莫斯科出席苏联文学国际翻译研讨会,那是1983年,苏联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次苏联诗歌译文朗诵会。当我在台上用汉语朗诵罗・罗日杰特文斯基的诗时,发现他用手指轻轻敲打原诗的节奏。显然,译文的节奏与原诗节奏不一致,他摇了摇头,又对我会意地笑了笑。我立刻意识到,诗的翻译在拍节上出了毛病。
1984年,叶夫图申科来我国访问期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国际俱乐部专门为他组织了一场他的诗歌朗诵会。那天,听众要求他朗诵几首计划外的诗,他毫不迟疑地便背诵出来。这使我感到惊讶。我问他:“那么多诗,你都能背下来?”他说:“除了自由体诗外……”在交谈中,我发现他不仅可以一首一首地背诵自己的诗,而且还能一首一首地背诵他人的诗。我想,这是他严谨创作的结果。叶夫图申科朗诵时,手的动作较多,特别是手指的动作,眼睛也时而眯缝起来,时而睁得滚圆。更值得注意的是音色,他的音色变化使诗增加了情感频率。
我还听过伊萨耶夫为艾青一个人背诵他的情诗《致妻》。那是在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欢送苏联代表团的招待会上。他的声音是那么柔润,那么多情,那么妩媚,缭绕于耳,战栗于心。
一次又一次与苏联诗人接触,特别是聆听他们的朗诵,使我不能不反复考虑如何翻译他们的作品,如何表达他们的个人特色,如何注意声调与音色以达到相近的效果。
到了晚年,我认识到,即使从事笔头的译者也必须通晓口语,否则在译文中会缺乏语感,甚至会出现误译。
离休――真正创作的开始
60年代初,我调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前前后后在那里工作了二十七年。1989年离休,那一年我六十三岁。
我是从业余文学爱好者走进外国文学专业队伍的。专业首先要求我付出更大的精力、更多的心血来充实自己所缺乏的系统知识。
《世界文学》杂志(原名《译文》),最初归属于中国作家协会,1962年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努力使杂志解除多年的禁锢,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外国文学的真实现状、热点、新的理论与流派,促进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沟通,从而繁荣我国的文学创作。
我曾与文艺界人士接触较多,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作画的机会。我画了一些肖像,除了我国作家的肖像之外,我还为外国文学家,特别是俄苏文学家创作了不少肖像画,如普希金、赫尔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人。我也画过不少同时代的苏联作家与艺术家。
离休,给了我充足的时间进行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我可以从早到晚专心于一事,没有迫切的任务需要完成,没有繁杂的行政事务缠身。往事常常涌上心头,于是我便着手写了一些随笔和回忆文章。年轻时,作为口译者,对很多事务领会不深,但作为见证人却记忆犹新,如果再不把当年的经历记录下来,有些珍贵的情景可能随着人去而烟消云散。我尽自己所能,把保留在脑海中的往事写了出来,基本上写的都是与苏联或俄罗斯有关的往事,其中写了茅盾、巴金、老舍、曹靖华、梅兰芳、丁玲、冰心、戈宝权、华君武等先辈访问苏联的文章,写了我与外国文艺界人士接触的回忆,出版了几本随笔集。这是我真正创作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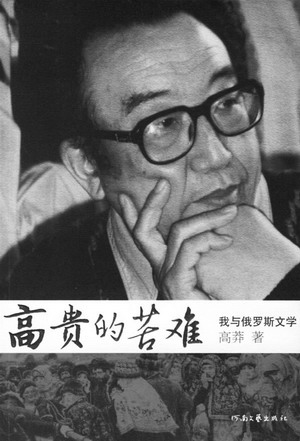 绘画是伴我一生的业余爱好。我之所以能够完成几幅大画,也得力于离休给我的时间。纪念梅兰芳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
赞梅图》与《巴金和他的老师们》,每幅画上都有十几位到二十几位真实人物,其中不少人是俄罗斯作家或艺术家,每幅画长达五米,高两米。能画出这些人物是我长期研究俄苏文学与艺术的结果。我必须了解每位俄罗斯人的生平、活动与画中主要人物――梅兰芳与巴金的关系。几个月的作画过程得到观众,包括俄罗斯友人们的赞许。
绘画是伴我一生的业余爱好。我之所以能够完成几幅大画,也得力于离休给我的时间。纪念梅兰芳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
赞梅图》与《巴金和他的老师们》,每幅画上都有十几位到二十几位真实人物,其中不少人是俄罗斯作家或艺术家,每幅画长达五米,高两米。能画出这些人物是我长期研究俄苏文学与艺术的结果。我必须了解每位俄罗斯人的生平、活动与画中主要人物――梅兰芳与巴金的关系。几个月的作画过程得到观众,包括俄罗斯友人们的赞许。
80年代我放弃了油画,改画水墨画,是因为我的妻子忽然闻到调色油的味道就会全身过敏。
我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时,用的是笔名“乌兰汗”,我作画时均属名“高莽”。有人把我真的当成了美术家。记得我在《世界文学》担任主编期间,有位读者来信质问 :“偌大的中国有那么多外国文学工作者,怎么竟找了一个美术家当主编?”好心的读者错怪了我。
我一生中以研究、介绍俄苏文学艺术为主,创作的主题都围绕着苏联和俄罗斯内容。
人虽然不能预算自己的出生日子,但可以估计自己将离去的时间。我已年满八旬,想做的事似乎还不少,但体力与精力都不济了。不过只要头脑不糊涂,我不会放下手中的笔,将沿着命运为我安排的路――与俄罗斯的情缘之路继续走下去。
(摘自《高贵的苦难――我与俄罗斯文学》,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