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2年,左起:张治中、周恩来、付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合影
黄埔斗争
一九二四年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遂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
不久,校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展开,在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属于中共方面领导的;一是“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至于我,实在说,是站在中间偏左,因此遂为双方所不满,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我常加攻击。中共方面,在事实上对我表示不满的只有一次,就是一九二五年春天,戴季陶、沈定一到校召开座谈会,中共对他们很过不去,使其下不了台,最后是我出来解围。我当时所以这样做,只是基于一种感情作用,绝没其他含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主人不应使客人太难堪(当然,我当时的立场是不明确的)。事后,在我领导下的中共干部许继慎曾告诉我,中共方面对此表示不满。此外便没有听过他们对我有其他任何的抨击了。
斗争越来越尖锐,以后遂演成了廖仲恺的被刺,“三二○中山舰事件”(事后听说,当时广州方面逮捕恽代英、邓演达、高语罕和我四人的手令已下,后因我们不肯应约登舰谈话,蒋又恐强行逮捕,激起学生的抵抗,遂作罢论),周恩来的辞去政治部主任等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一九二五年夏,我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我的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因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我喊作“黄埔四凶”。就在这时候,我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首先向周恩来先生提出。他当时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我回话。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大意如此,倘使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件事当然经过中共的讨论的)。
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
一九四○年九月,我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政治部这个机构是在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恢复设置的。当时还具有两党合作的一些形式和作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在第三厅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文化人。我一向对左派文化人采取同情和维护的态度。一九四○年在我接任政治部部长之后,当时就有人主张把郭沫若这一派排挤出去,但是我并不以为然。我以充分的理由说服了建议的人,并且主张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朋友。当时我还曾和郭沫若先生说了一句笑话:“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这虽是笑话,但也可以反映出我的心意。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还和他们谈了几个钟头,给他们解释安慰,并还约定和郭沫若两周谈话一次。谈话是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大家都觉得满意。
以后据某方报告,说他们“思想大都左倾,时与共产党接近,特别是郭沫若、一部分委员和各组负责人”,认为“会内有真正共产党分子在活动”。其事实是:“会内常发现共党刊物,刊载攻击三民主义青年团文字;新四军事件发生,言论多同情共产党;用辩证唯物论分析各种问题;用共党思想写作戏剧诗歌;利用文艺活动吸收群众;宣传苏联制度及马列主义;德苏战争发生前,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竭力抨击英美;向《新华日报》投稿;翻译苏联及美国左倾刊物之理论文字;各种座谈会均有共产党参加”,等等。我觉得这些事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左倾文化人的“租界”所在,一切听之罢了。
不过,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为此我曾招待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我的话是从爱护的心理出发的,但是不久香港寄来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对我的谈话大加嘲讽,中有“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语。我看了感到难以索解,所以当时写信质问他:“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后来他客气地复我一信,加以解释,我也就不再和他争辩,不过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是渐渐疏远了。今天想起来,为这件小事而疏远朋友,是一件遗憾的事。
这个委员会内包括了不少知名之士,如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胡风、杜国庠、吕霞光、姚蓬子、郑伯奇、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都是委员。后由于我和郭沫若关系的逐渐疏远,使反对者更有隙可乘,最后由于某种压力和影响,我是感觉到这个机构在我的精神上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到抗日战争末期――记不清在一九四四年吧?――就把它撤销了。虽然对这些文化人都有了另外的安排,并建议蒋给郭沫若适当地位(如在中央研究院添设古物研究所,由郭主持),但未实现。这在我来说,是件有始鲜终、为德不卒的事,心里至今犹引为遗憾。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我到了上海,郭沫若先生也在上海,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共气焰高涨的时候,我特意请他和在上海的文化界朋友如田汉、洪深诸位在酒馆吃了一顿饭,虽然宴席间没有谈到时局和往事,但我的心意却在表达我过去对他的歉意和当时对他的慰问。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旋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是,毛泽东先生慨然电复应约。于是由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安去迎接。记得就在八月二十八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先生到了重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先生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毛先生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
起初,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但经过四十天的商谈,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就是十月十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所签订的外间叫做《双十协定》的文件。
毛先生在留渝四十三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在他要我代约时间宴请毛先生和同行诸位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在十月八日,我曾假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五百余人参加,盛况空前。
到十月十一日,我特送毛先生飞返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当天晚上,中共还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欢迎我,宾主尽欢。第二天毛先生亲送我到飞机场,在车上还带点幽默地对我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又重复在重庆时的话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我说:“何以见得?”他举了几个例子,并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6年3月4日下午军事三人小组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发负责人和数千群众的欢迎。左起:周恩来、马歇尔、朱德、张治中、毛泽东、林伯渠
马歇尔到了中国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马歇尔以杜鲁门特使的身份到中国来(这时赫尔利已调为驻华大使)。蒋果来电报,催我回重庆。一九四六年元月六日到重庆。
到重庆时,蒋已等不及,先派张岳军为代表,已和周恩来、马歇尔谈了几次关于停战的问题。张一见我就说:“本来你是代表,久候你不回来,才叫我暂代,现在你回来了,我可以交代了。”我说:“那不行,你们已谈得一半,我怎能插手?等你先把停战问题谈妥了再说吧。”停战协定于元月十日正式签订。并且随即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三方面会同组成。国民党代表是郑介民,中共代表是叶剑英,美方代表是罗伯逊。
就在停战协定签订公布的同时,根据《双十协定》所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日开幕,历时二十二日,总算获得了协议,于同月三十一日闭会。这时国民党政府已派我为代表,中共为周恩来,美方为马歇尔,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
会议从二月十四日开始到二月二十五日,前后正式会议和会外协商多次,最后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现在,我可以公开一件秘密。在商谈开始之前,马歇尔向蒋提出一个草案,这个草案马歇尔事先没有给周恩来看过。
大意是,改编之后,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也向未提过这种要求,草案则准予中共取得百分之三十的兵力。这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的。这份草案到蒋手上,蒋当然感到非常诧异,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率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就没提了。
方案的签字仪式是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重庆上清寺尧庐(即蒋侍从室所在地)举行的,当时我和周恩来都有简短致辞,马歇尔的致辞更简短:
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马氏的致辞虽只寥寥数语,但刺激性甚大。显然,他所称的“少数顽固分子”是指国民党方面的,大概他当时已经从情报方面得到若干的报道了。
为了贯彻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除了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办理派出许多三人小组分赴各地执行外,这时由周恩来、马歇尔和我三人坐专机到各地作了一次检查,先后到了北平、张家口、集宁、归绥、太原、济南、新乡、徐州、武汉、延安,然后再回到重庆,计历时七日。
三到延安
在这里,我特别提起这第三次到(前两次是接毛泽东到重庆和送毛泽东回延安――本刊注)延安的情形。到延安和离延安,毛先生都亲为接送。记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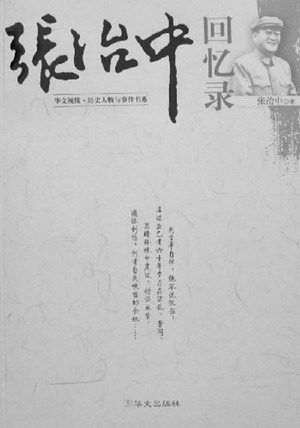 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有中外记者随行,后来曾在报上发表过),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后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曾被CC分子郑亦同所引用,颇有讥讽之意,我当时曾加以驳斥说:“如果郑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见解,我是愿意接受的;但如果是一种讽刺,那么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是准备来个七折八扣?”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以后还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我笑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毛先生说我还可以四到延安,虽然后来蒋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议,但未成事实,而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有中外记者随行,后来曾在报上发表过),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后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曾被CC分子郑亦同所引用,颇有讥讽之意,我当时曾加以驳斥说:“如果郑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见解,我是愿意接受的;但如果是一种讽刺,那么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是准备来个七折八扣?”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以后还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我笑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毛先生说我还可以四到延安,虽然后来蒋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议,但未成事实,而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摘自《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2月版,定价:5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