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家乡有一句流布很广的谚语,叫“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我以为,这实在是很见智慧的一种人生态度。试想,贫瘠的土地,纵是再努力耕耘,收成也是寥寥无几。贫穷之家,纵是再克勤克俭,积累终究有限。所以说,
让我困惑的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要指望能出个一心为民毫不为己的清官肯定不现实。我这么说,并非要反对穷人当官,而是要反对那些把做官当成脱贫致富、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的人。
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削尖了脑袋往官场钻,聪明的执政当局,在国家财政匮乏或个人腰包空乏时把官位市场化,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乾隆三十一年政府的部分岁入情况为:地丁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余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余万两。
地丁即农业税和人头税,耗羡为损耗附加税,盐课即官营和政府专卖收入,关税是物品跨区域流通的通关税,落地税和杂税等同于现在的特产税,契税古今事同,牙、当等税为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费,矿课为矿山开采费,除此之外的常例捐输,就是政府为弥补财政的不足而强征的税,大多是卖官鬻爵所得。这部分收入,约占当年度总岁入四千多万两的十三分之一,比例不可谓不高。
在我泱泱中华,卖官鬻爵的历史可谓久之又久,自《史记》始,即有“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这是最早出现的鬻爵。
汉文帝时,匈奴屡次犯边,在边疆戍守屯田的军队日增,政府却连最起码的粮食供给都无法保证,文帝用晁错的建议,招募有能力捐输或转运官粮到边疆的人,可以授爵,所授的爵位,最高可以到大庶长这样的级别。(事见《史记・平准书》)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意思是,爵位这东西,是皇上所专有的,只要皇上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拿来封赐给人们。所谓的爵位,不过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罢了,这样的买卖对朝廷来说不啻是一笔无本的生意。
爵位在民间的自由交易也是汉文帝时的事。《史记・孝文本纪》中说到文帝在位时,天下一度旱、蝗连年,于是文帝特别加惠,其中就有允许民间自由买卖爵位一项。(《史记索隐》引崔浩的解释说:有钱人希望得到爵位,穷苦人希望得到实惠,朝廷只好就放任这样的交易发生。)
景帝时,上郡以西常发生旱灾,政府又一次颁布卖爵令,并把价格降得很低,以广招徕。
由此可见,秦汉时的鬻爵其实是指用爵位来换取粮食,目的是援助军粮或救灾,政府并无现金收入。可以说鬻爵是国家在财政匮乏时,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卖官则始于汉武帝时期,《史记・平准书》记载:元朔五年,主管官员征得武帝同意,宣布设置赏官,定名为武功爵,如有买武功爵到第五级“官首”者,可以试用为候补官吏,遇有职位出缺即可补任。
这是由鬻爵到卖官的偷偷转换。可是,当时的政府碍于视听,还不敢公开卖官,然而,事情发展到东汉桓、灵二帝时,便大不一样了。
《后汉书・桓帝纪》有这么一段话:延熹四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占,根据《辞源》的解释,意为估计上报,如《史记・平准书》有“各以其物自占”的话,自占,意即自我报价)占卖,即出价竞买,形式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竞标,这不能不说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大概是桓帝时官爵太滥,到他儿子灵帝当政时,卖官的行情便大不如前,史料上说,当时有钱人买官可以先交钱,无钱的可以赊欠。不过到任后得双倍奉还。
有一次,灵帝把三公之一的司徒贱卖了,过后,还心痛了好多天。《后汉书・崔烈传》说,崔烈靠了灵帝保姆的推荐,只交500万钱,就当上了司徒。按照当时标的价码,要当司徒至少得1000万钱,如此看来,这显然是让崔烈捡了个大便宜。这事弄得灵帝闷闷不乐,可是君无戏言,又不能反悔不卖。到崔烈拜官那天,灵帝还念念不忘地对左右亲近的人说:“我若稍微吝惜一点,1000万钱就可以到手了。”(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还有一个卖官的活宝,是南朝刘宋时的大贪官邓琬。邓琬因拥立晋安王刘子勋称帝有功,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在权力到手后,为尽快敛财,他干脆命令自家的奴仆,把官位直接拿到市场上去卖。(事见《宋书・邓琬传》)
官位可以竞标,可以赊欠,可以钱滚钱,还可以直接到集市上去卖,你要说这官位不是产业还真说不过去。
官位既然是一种产业,投资的方法自可因人而异:
有些人可以靠苦读当官,就是马二先生所说的,在举业上下功夫。苦读既费时又费力,时间和精力同样是一种成本和投入,时间属于机会成本,精力则是直接成本,这中间还得再加上未必考得中的风险成本,所以说苦读的代价最大,这是穷人的方法,有钱人不会这么干。
穷人的另一个常见的仕进之法,是给当官的做幕僚,付出的同样是时间和精力,可是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风险成本会大大减少,这是改守株待兔为主动出击,成功的机会自然就多一些。
有钱人的唯一优势是有钱,有钱人要想当官,除了直接投资之外,一般都会独资干。这当然是首选之法,也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方法。所以先赚钱后当官风险最小。
无钱的要当官,可以借债,旧时北京城里有的是放京债的,通常的利息是二分,当然也有高到“倍息称贷”的。
借不来钱又想当官的,还可以大家凑份子,合伙来干。
我说的合伙当官,绝非笑话,更不是无的放矢。明人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还专门说到这法儿,为免生误会,我把原文抄录如下:
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
我原以为这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的。可是,偏偏在现实中,就有这样的咄咄怪事。
有一则清代轶闻说,浙江山阴人蒋渊如看到买官可以一本万利,却苦于资金短缺,就与其友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四人合计。五人集资捐了个马上就可以补任实缺的知县。并在神前歃血立盟,互道永不相背,并议定具体的分工办法:蒋任县令,唐为刑名师爷,陈为钱谷师爷,王为钱漕吏目,吕为转递公事的快手,如此,合五人之力,管一县事务,无论具细,悉在掌握中。得赃,则按出资比例分肥。上任之后,按议定的分工,蒋以县令之尊高坐大堂,待唐、陈二人以幕友,视王、吕如奴仆,各无怨言。五人通力合作,上下其手,一年收入便达白银二十万两。三朝任满察考蒋虽以贪墨丢了乌纱,五人却如愿以偿,挣了个盘盈钵满。(事见徐珂《清稗类钞・爵秩类》之五人公捐知县条。)
要说蒋渊如等人是受了冯梦龙的启发,似乎不大可能,冯的小说在清代是禁书,一个生意人,断没理由冒着屁股挨揍的危险去接触黄色读物。那么,可能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蒋渊如等人聪明透顶,无师自通,干的跟前人书里说的一模一样。再就是所谓的集资买官,原本就是个普遍现象,有如生意中的合伙,纯属正常。
据南宋史家洪迈考证:南宋开国初年,仅有京朝官三四千名,选人七八千名。绍熙二年,在籍的官吏即有: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名,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名,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名,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名,官吏总数为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名,是国初的三倍。到庆元二年四月,除京官人数未变外,选人净增八百零一名,大使臣净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名,小使臣净增七千四百名,尚不计算当年科举入仕的名额,短短四年时间,官吏人数已激增近万名,增幅为30%以上。(见《容斋四笔》卷四,今日官冗条。)
明末的南明小朝廷因为财政吃紧,便狠命地卖官,弄得大街上全是穿官服的,当时有民谣曰: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跑。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
日本学者宫琦市定在《清代的胥吏和幕友》里说,清代的典吏或称经承,作为县衙各房的负责人,他们承包了县衙的一个部门,拥有私人雇佣的几十个徒弟(即“白役”或“白书”、“贴写”、“挂名”等),将处理公务必需的文件当作私有财产垄断起来。
县官虽有监督经承的责任,但既然是承包制度,经承对徒弟的人事安排,县官就不能干涉。而经承往往收有亲戚关系的子弟为徒,在引退时把其职位让给这些子弟,于是就形成了胥吏职位的世袭化。
接着就引起了职位的买卖,称为缺底买卖。经承在职位不传给子弟而让给他人时,要索取出让金。而且这种权利出让不是完全出让,只是允许在一定期限内使用权利。这种家族传承的权利,称为世缺,所有者称为缺主。世缺或缺主的说法,始见于雍正元年的上谕。
官吏的职位可以像私有财产一样,拥有产权的一方,有处置权、使用权、继承权和获得收益的权利,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所特有的官场怪现状。
以上说的是官府公开的卖官行为,还有一类是私下相授受的跑官。
官位的私相授受的始作俑者,依旧是汉灵帝刘宏。
《后汉书・灵帝纪》载:“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由此可见,灵帝卖官,一公一私,公者交易地在西园,出榜公布,明码实价,这部分收入归少府所有。私底下的那部分收入,则成了灵帝的私房钱。灵帝还没当上皇帝时,本是解渎亭侯,据说待遇不怎么好,大概经常缺钱用,当了皇帝,便拼命地攒私房钱,这些钱有的拿回了灵帝的老家河间府置办田产和房产,有的托付给小黄门和常侍代为保管。(事见《后汉书・张让传》)
明代吏科给事中韩一良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说: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的话。可是现在这世道,哪一处不是用钱的地方?现在这社会,哪一个不是受钱的官?皇上也知道文官不得不爱钱吧?什么缘故?他们原本就是靠钱进来的,哪能不用钱来偿还?我听说现在的一任督抚,没有五六千两银子得不到;道府的美缺,没有二三千两银子得不到;甚至州县和佐贰官员的现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和吏承的选拔,也要靠贿赂才成,所以说吏部的工作就可想而知了。就连中央的各科道职位亦有一半以上要用钱来买,公开的选举也是一个样。(谈迁《国榷》卷八十九,崇祯元年七月辛酉条,韩一良的原话是: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一语。然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 又何官非受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所闻见,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得之,馆选亦然。)
这一连串的“甚至……就连……”,告诉我们的事实只有一个,那便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
同样的记载也见于李清的《三垣笔记》:有一个小吏用了五千两银子运作边镇巡抚的官职,钱出手后就怕出价过低,于是追加了二千两,马上得到了理想的职务。有一个部的郎中,谋求浙海道的官职,吏部的人要价白银五千两,那人压价,只肯出三千两,虽然只出了一半多的钱,最后也如愿以偿。县令中有钱的,想进礼部当曹员,得花白银二千两,想进兵部当曹员,得花白银一千两。
明代的改革派领袖张居正,便是以太监冯保为政治靠山,“得委任,专国柄”的。《天水冰山录》中说,因为冯保弹得一手好琴,张居正便让儿子张简修送给他名琴七张,因为冯保贪财,张居正又让儿子张简修送给他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此外张居正贿赂冯保的另计还有黄金三万两、白银十万两。
一代名相张居正,居然要靠向刑余之徒行贿来邀宠。 这便是跑官对整个官场生态最致命的破坏。这样的破坏让一些原本大有作为的好官出淤泥而皆染,见利益而不免俗。
右手出钱,自然得左手进钱,正如韩一良在上文中说到的,这些钱不会从地下冒出来,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出得愈多,职务愈大,进项自然也就水涨船高,这一进一出之间的差额,便是贪官的受益部分。
如果没能把握住收益的正常周期,这个部分就有可能为负数,果真如此,纵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有人愿意去做官。
我国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件畏官场如畏刑场的奇闻逸事。
元至正年间,朝廷派兵部员外郎刘谦到江南卖官,补充各路府州司县出缺的官位。自五品至九品,各有不同的价格。这些职位官职虽大,油水却不多,所以没人应征。松江知府崔思诚为了巴结朝廷大员,硬是领了十二个名额,然后把松江府所有有钱人集中起来,硬性摊派,结果被点到名的无不哭穷,崔无法,只得大刑侍候,一顿板子打下来,才算把所有的名额卖了出去。(事见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
做官还有一个途径,说起来有点邪门,那便是做贼,这里所说的贼,精确地说应该叫做匪。这便是宋谚所谓的: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先做贼后做官,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仕进之路。贼做得愈大,招安时,给的官位也愈大,若是贼首,做了官必定还会是一方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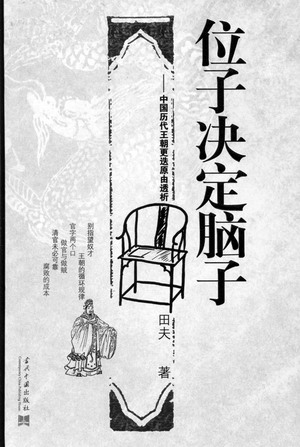 《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占山为王时,便排有座次,一号宋江,二号卢俊义,三号吴用……受招安时,当局依旧要按原定座次来授官,一点也不含糊,一号还是宋江,官拜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二号卢俊义,官拜武功大夫,庐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三号军师吴用,授武胜关承宣使……
《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占山为王时,便排有座次,一号宋江,二号卢俊义,三号吴用……受招安时,当局依旧要按原定座次来授官,一点也不含糊,一号还是宋江,官拜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二号卢俊义,官拜武功大夫,庐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三号军师吴用,授武胜关承宣使……
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其编撰的《史》中说:海盗郑广,在莆田和福州一带啸聚亡命之徒,能以一当百,官军不能战胜。自号滚海蛟。皇帝老儿下诏招安,赏给他一个不大不小的武职,容他效命朝廷。由于郑广做过海盗,同僚们对他无不侧目而视,没有谁愿意搭理他,这令郑广大为窝火。有一天早上,郑广进衙办公,见同僚们聚在一起谈诗论句,便主动搭讪道:“我郑广是个粗人,作了首歪诗,想献个丑,念给诸位听听,不知可否?”当大家凑过耳朵,郑广便大声朗诵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听到这里,众官吏又惭愧又说不出话。故事结尾,作者借时人章以初之口说道:“今天下士大夫愧郑广者多矣。吾侪可不知自警乎。”做贼的居然比做官的还理直气壮,这实在是对旧时官场的一个绝妙讽刺。
(摘自《位子决定脑子――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原由透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7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