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大革命”中的振环阁店内
一九六二年我参加工作的那年,北京文物商店刚从四店合一的“新华书店、中国书店、外文书店、文物商店”四马分肥的联合体中独立出来
我们这批共有五名学生被分配到文物商店。这可是解放以后古玩行招收的第一批学徒,我被分配到了新街口的悦雅堂。
悦雅堂是离琉璃厂文化街最远的一个门市部,和琉璃厂文化街上那些专业门市部[如专营古代书画的宝古斋、专营现代书画的墨缘阁、专营金石陶瓷的韵古斋、专营历代碑帖砚墨的庆云堂]不同,它是个综合门市部,有字画、碑帖、陶瓷、杂项等,同时,因为既收又售,综合了琉璃厂所有门市的特点和功能。
悦雅堂当时的工作人员共有五位,徐震伯师傅、谢子陶师傅、曹文铎师傅、赵嘉章师傅,这都是所谓的私方人员,还有一位姓安的公方人员,算是负责人。我去了以后,悦雅堂就有六人了,而我的学徒生涯也从这里开始。
文物商店的从业人员大都是解放前后古玩行的业主,按照国家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公私合营时结合进来了,百分之九十都是大小资本家,也是一辈子从事“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古董生意的各路高手。这些师傅们在一九六○年五月一日文物商店成立后不久,就被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等单位聘为专家顾问,有的也是文物商店的工作人员。故宫博物院书画征集部门的已故专家王一平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健在的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权威耿宝昌先生,都“出身”于琉璃厂,在这个意义上,琉璃厂真可以堪称是我国培养文物鉴定人才的“黄埔军校”了。
古玩行对我们新来的来说也真是新鲜,全店那么多老师傅,就我们几个小青年,格外显眼,至于拜师学徒,那真是僧多粥少,师傅多徒弟少,我们这几个学徒工成了宝贝“粥”了。就这么着,悦雅堂的四位师傅都成了我的老师。
徐震伯师傅是我的首任老师,他那时五十来岁,他“出身”于琉璃厂大字号明珍斋,鉴定明清书画及宋元明清陶瓷是他的拿手好戏。
第二位老师是谢子陶,六十多岁,他的特长是书画、碑帖鉴定。
说来也巧,我学徒不久,康生就在悦雅堂放一般拓本的货架上翻出了一个拓本,名字记不起来了,标价才十几元,康生当时就买了下来,也没说什么。
等过了几天,专营碑帖的庆云堂就打电话来问:“你们是卖给康生一个拓本吗?”
我们回答:“是啊!”
“那是个宋拓本,值四五千元!”
“完了,完了,漏了!”师傅们惋惜地说。
四五千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当时一幅郑板桥画竹石的大幅中堂才一百元左右呢。可惜,太可惜了!
曹文铎师傅那时已六十多岁,他的特长是瓷器、杂项。
听曹师傅说,解放前为了买一只瓷瓶而不暴露目标,竞把卖家的一大堆瓶子都买了,装了整整一汽车。还有一次,他的女儿要出嫁,为给女儿办嫁妆,就出去到处溜。德胜门前,过了护城河上的桥,桥头西北角有一个卖馅饼的食摊子,食摊子上,一个大瓷盘上放满了馅儿,曹师傅走到食摊子前,看到了这个盛馅的盘子。
他不动声色,买了个馅饼,一边吃一边搭讪着和掌柜的说:“掌柜的,你的馅饼很好吃,下回还来。”
掌柜的一听,当然高兴。
过了一会儿,曹师傅又对卖馅饼的说:“掌柜的,我看这瓷盘子您每天在上面‘乒乓’地抹馅,没准儿哪天就给 [cei]了,一钱儿不值,我给您买只搪瓷的盘子,又结实又好看,您把这个瓷盘给我,我挺喜欢这盘子,咱俩换换,您看行吗?”
曹师傅说这话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掌柜的一听,拿搪瓷的新盘子换他的旧盘子那当然值了,要知道搪瓷的东西在当时还是稀罕物呢!于是立马儿就答应了。卖馅饼的做梦都没想到曹师傅是干什么的。
“你猜怎么着,小陈?我拿着换回的这只盘子卖了几千大洋,宣德青花,那可是宝贝啊!把姑娘嫁了,还剩下很多钱。”他一边画圆圈似地晃动着身子,一边满脸得意地讲述这段得意的往事。
还有一位师傅是赵嘉章,琉璃厂韵古斋出身,五十多岁,他是明清官窑专家,眼睛厉害得很。我很喜欢这位师傅。
唉!如今我的这些师傅们都不在了。想到这些几十年前的往事,真有恍如昨日的感觉啊!
有一天,我和曹文铎师傅看门市,来了一位顾客,拎着一个包儿,进门把包儿往八仙桌上一放,曹师傅知道他是来卖东西的,就说:“请您把包儿打开。”
行里规矩,卖货的不管是谁,一定要让他自己打开包儿。
那位卖东西的打开包儿,原来是一件类似宜兴茶盘子或文具盘的东西。
曹师傅一看,不动声色地说:“你要出让?”
对方回答:“是。”
曹师傅说:“那好那好,这个茶盘很容易碎,再说脏了也不容易洗,您看,上面的蓝墨水就洗不掉了。”
我一看盘子的上面的确有一圈蓝墨水儿的痕迹,兴是放墨水儿瓶的结果。卖东西的很快就出让了,可能仅十几元钱。
顾客刚一出门,曹师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兴奋地对我说:“小陈,赶紧拿后面去,明天送故宫!”
我一愣!“这是什么宝贝呀,能送故宫?不就是个茶盘吗?”
“你看这文字,这是有名的《河洛图盘》,杨彭年制,这可是重要物件,是真的!”
我也立刻注意起来,盘子上面刻着文字:
杨彭年,清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江苏宜兴人氏,善制砂壶,其壶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若寻常贻人之壶,每器只二百四十文,加工者价须三倍。
我大吃一惊,曹师傅这不是给姑娘凑嫁妆的故技重演吗?眼睛这么厉害!好家伙,真是神了!我也不敢怠慢,拿到后面内柜,找了纸墨,做了个扑子,就把文字、花纹拓了下来,这张拓片至今还保留着。
第二天一早,送到故宫后,他们立刻就收购了,而且价格不菲。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旁观了古董买卖的全过程,印象很深,觉得很兴奋,并暗下决心,得好好干。
看到这儿,您可千万别误会,您可能会认为,怎么你们文物商店还像解放前的古玩商那样,干那种“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低买高卖的勾当。不是的,文物商店成立以后,我们收购的是流散文物,由于经历了社会大动荡,有时老百姓手里的重要文物[也就是宝贝吧],因为老人故去,后人大部分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随便几个钱就给卖了,但真的向他讲,您这东西值多少多少钱,他反而就没底了,以为还值更多的钱,不卖了,那么这件东西可就玄了,结果会不得而知。为了不发生这种情况,收购时先低价收进,再按卖主户口簿的地址去给补钱,曹师傅就是这样干的,您可别见怪。
有一天早上门市开门后,打扫完卫生,我隔窗往外望去,忽然注意到有两个男子一前一后,向悦雅堂走来。于是赶紧开门迎接。
“您好,老徐在不在?”走在前边的那位年轻人用很浓重的四川话问我。
“在――”我回头喊了徐师傅一嗓子。
徐师傅从内柜出来,一见年轻人,脸上堆满了笑:“您好,田秘书,陈秘书,请进!”
等二位都进到内柜后,徐师傅临进去前回身小声儿对我说:“毛主席的大秘书”。
“噢!怪不得。”
自打那以后,田秘书和陈秘书常来,他俩总是形影不离,我也就和他们慢慢熟了起来。田秘书就是田家英,陈秘书叫陈秉忱。
我很喜欢田秘书和陈秘书,他们身上没有一点架子,和你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是和蔼的,似乎还有点腼腆的表情。
他们来这里,无非是找些他们喜欢的书法、信札,或有用的资料。为了表达对他们的热爱与尊敬,我就有意留心这些东西。田秘书特别注意明清两代的书法,如字条、对联、书札、手卷,他都喜欢看,而且这些东西很便宜,几元钱、十几元钱就能买件很有名气的书法作品,现在王铎一幅字轴能卖到十几万、几十万,那时十几元、几十元就可买好的了。
有一天,田秘书和陈秘书相随而来,我忙把一副包世臣的对联拿给他看。我问他:“您喜欢吗?”
田秘书很专注地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小陈,这副对联有问题,不对。包世臣的字肉多但有骨,这副肉多无骨――软,下次我带副他的字你比较一下。”
我当时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对一个小青年哪会认真到这种程度,真没想到,没过几天,他真的带来一副包世臣的对联给我看,让我把店里的那副拿出来,两副挂在一起比。这一比,显然大不一样。我心里想,田秘书又不是书画鉴定专家,他的眼力怎么这么好呢?
他不但自己选些字对儿什么的,遇到好点的碑帖、字条,他先送给毛主席看。
有一次,谢子陶师傅下户采购,拉回一三轮车[人坐的那种三轮车]碑帖。这批货一律的瓷青帖面,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有一套《三希堂法帖》,三十六本分装四个箱子,一色的楠木面,楠木箱。正赶上田秘书在,他就在车上看了看说:“等定了价,给老板送去。”
他们称毛主席“老板”;毛主席身边的人都这样叫。
就这样,你来我往的。我和他们这些大首长越来越熟了。有时他们来的人多,店里就我一个人,怎么办?我就把他们让到后面的内柜,把所有的抽屉、柜子打开,让他们随便看、随便选,我一个人到外面去,保证他们的安全,反正都是首长,没有问题。

你看田家英不但文章写得好,人也长得帅气。
“田秘书,听徐师傅说,你十三四岁时在成都药店当学徒,在报上为一个学术问题和一位名教授展开辩论,最后您把那位名教授驳倒了,那位教授非要见见这位对手,见面一看原来是个孩子,惊呼您是神童,是真的吗?”我问他。
“真的,真的。”陈秘书在旁边笑着说。
“啥子真的,他不叫我神童怎么下台么!”田秘书笑着搭讪。
悦雅堂虽说规模较小,但由于是综合门市,所以各界人士来这儿的很多。除了像田家英这些首长以外,我很快发现,经常来悦雅堂的还有几位老先生,像大书法家傅增湘的后人傅仲模,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小老头儿关祖章,还有一位一米八左右的老先生孙老。
他们几位时常光顾悦雅堂,有事没事就来店坐坐,喝喝茶,聊聊天,有好东西了,就拿给他们看看,真有点像老舍写的《茶馆》里的景象。
傅老那时已经很老了,拄个拐棍,背也驼了,喜欢玉。他是个玉器收藏家,玉件拿在手里,一看就知好坏,所以即使东西已经收进来了,店里的师傅也要请他老人家掌掌眼。
一天,推门进来个五十来岁的人,身穿一身蓝色干部服,头戴蓝色干部帽,白白净净的脸上戴一副黄边眼镜。在当时,在人群里身着这一身打扮,就像一滴水滴入了大海,很难再被分辨出来了,但那位先生身上特有的气质却非同寻常。
“启先生您好,您好。”徐师傅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
启先生手提一小纸包,眯着眼笑眯眯的,见到徐师傅及其他人都规规矩矩轻轻弯腰鞠躬,真是和蔼极了。
“您好!您好!”启先生也答应着。
徐师傅说:“老没见您了。”
“没事,随便看看。”
他一边说,一边把手中的纸包放到八仙桌上,再把帽子脱掉,也放到桌子上。
徐师傅问:“您这是什么好吃的呀?”徐师傅看着桌上的纸包儿。纸包儿上已有油渍浸出来了,散发着酱肉的香味。
“我在隔壁稻香村买了点酱肉,嘴馋!哈哈。”启先生眯起眼睛笑着。
“您很长时间没来了,想找点什么看看?”徐师傅一边陪着启先生,一边搭讪着。
“是、是、是,有点忙。我没事,随便翻翻,您甭陪着我,谢谢,谢谢!”

苗子先生一晃九十多岁了,生日聚会上李瑞环、郁风等为其庆祝。
这个老头一看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特别随和,有礼貌,还有点幽默,他一个人在帖架子上随便翻看着,旁边的师傅们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启先生闲聊着。我在一边想,这位启先生会不会是启功先生?
等快关门了,启先生离去,我就问徐师傅:“这是不是启功先生?”
徐师傅说:“是啊!你不认识?”
“不认识,知道这名字,没见过。”
“有阵子没来了。”徐师傅说道。
自打那次见到启功先生以后,我就经常见他来悦雅堂,他好像都在下班前后来,每次,多半都买一包稻香村的点心、肉食之类的东西。慢慢地,我就和先生熟了起来。
一九六四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我与赵存义、李心田二位师傅一组,到成都采购。住下不久,我们就开始和当地文物店、客户联系。客户,就是当地有古董字画的人家,准备出让的专等我们来,原因是那时这些人家并不愿意让当地人知道他家有什么,卖了什么,再者,我们在收购时要比当地的价格高得多!
我们到当地文物店后一看,东西可真多,旧墨、旧砚摆满了柜台。墨呢,一盒一盒的,很多是明朝墨、康熙墨,一绽只卖几块钱。再看那砚台,多是乾隆“子儿石”,天地盖也很讲究,一水儿的整挖,不是梓檀就是黄花梨的,很少有一般木质的,砚台很多有刻铭。再看,那些古董、书画,也便宜得很。
我们下户收购才知道,收藏二三百方砚台的藏家,在成都不算什么稀罕事。二三十元钱就可以买到一方硬木盒子“子儿石”砚。我们就足足地一收,成箱成箱地发回北京,心里真是美滋滋的。这些货运回北京,售出的价格都能翻十倍、二十倍,要是留到现在更甭说了。书画也是如此,但没这么多,大幅的徐悲鸿画的七匹马才卖七十块钱。
在成都,我有幸认识了刘少侯老先生,他可是张大千的得力助手。张大千造的假画,凡是宋元、石涛之类的旧画,其旧裱工完全出自老先生之手。张大千出国后他留在国内,那时就在成都博物馆干他的裱画行当,五十多岁了,孤身一人,好喝酒,无论走到哪儿,兜里总装着一瓶“回沙郎”[就是现在的“郎酒”],极普通的包装,两块多钱一瓶。他是北方人,遇到我这个老乡,分外亲切,一有机会就拉我一起吃饭、喝酒。
一九六五年初,我又和李孟冬师傅、王鲁师傅三人一组去江浙一带采购,首先到的是上海。
李孟冬师傅是我常常想起的人之一,我虽没有正式拜他为师,但仍在李师傅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他看起画来,干脆利落,毫不犹豫。他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落款上,只要款子没问题,他很快就能断定下来是真是假。
前些日子,我到黄苗子黄老那里去。黄老都九十多岁了,我看他忙得很,手里拿着一沓子纸张,就问他:“黄老,您在忙什么?”
他说:“我正在整理‘八大’的年表,最近就要出版了,你看,这是启老送我的八大山人字帖。”
我接过来一看,上面有李孟冬的字样。
“这是李孟冬送给启老的,好多年了。”
“黄老,这是我师傅,他在世时我们常一起出差。”
“是吗?那太好了,这人了不起,眼睛厉害,你知道吗?早些年李孟冬在上海买了一张元朝倪云林的山水画,行里人都说不好,等后来张珩看到了这张画,说这是真的,是张好画。李孟冬当即表态,白送故宫。您看绝不绝,真是的。”黄老这个小老头儿说起这件事,满脸放光。
我们三位在上海期间照例到文管会报到,到上海古玩市场、朵云轩等处选货。上海的朵云轩其实是北京荣宝斋的分号,当时的经理叫梁子衡。在他那里选了一些货后,很快转到杭州。
我们到杭州文物店去办事,一进门,看到店堂里很多人,再一看,嗬!几乎都认识。康生、陈伯达、田家英甚至还有胡绳等都来了,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还是田家英先看见了我,眯着眼睛笑嘻嘻地问我:“小陈,您来这里做啥子吗?”
“来采购”,当时我没深没浅地也问他们,“您们干什么来了?”
田家英仍然笑眯眯地说:“我们也来采购嘛。”说完,康生、胡绳他们一起哈哈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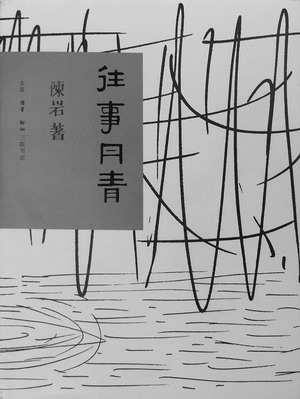 这一年是一九六五年。在我们遇到田秘书之后不久,还没有离开杭州,突然天降大雪,气温骤降。据当地老百姓说,杭州地区六十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西湖四周的景色都被大雪盖了个严严实实。
这一年是一九六五年。在我们遇到田秘书之后不久,还没有离开杭州,突然天降大雪,气温骤降。据当地老百姓说,杭州地区六十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西湖四周的景色都被大雪盖了个严严实实。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呢?因为这段记忆正好和我们国家要发生的重要事件联系起来了,在不久后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才从大字报、小字报和各种宣传材料中得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会议,史称“十一月杭州会议”。这次会议就是为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
我也万万没有想到,杭州那次见面竟是我和田家英相见的最后一面了,当时他笑得那么开怀,他是那么年轻,那么有风度,那么潇洒,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
我的学徒生涯到了一九六五年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即将进入尾声,而我们的国家也即将进入一个异常艰难的历史阶段,并长达十年之久。
(摘自《往事丹青》,三联书店2007年8月版,定价:4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