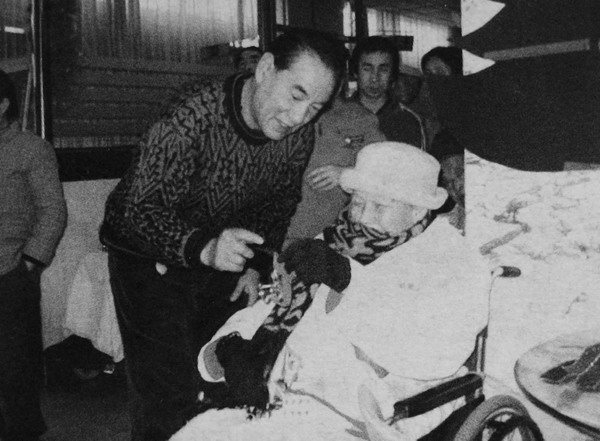
曾经健壮鲜活、美丽年轻的生命,如今身处死亡的边缘,谁来倾听他们最后的绝唱?
1967年7月,英国女医生西塞莉・桑德斯博士在伦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临终关怀医院――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到今
这家医院,人们可能见多了生生死死,但恰恰在这儿,生命显得格外的有光彩并且鲜活。
北京松堂医院是中国成立的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在这所医院里,平均每天要送走两个人,平均每个人的住院周期为三十一天,最小的病人是五个月大的女婴。现年五十六岁的李伟是这所医院的创办人,在医院成立以来的十九年里,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送走了近一万七千人。
1968年,十九岁的李伟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农村插队,成为了当地的一名赤脚医生。他的病人里有一位患晚期肝癌的老知识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批斗下放到农村教书。临终前老人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只要神志清醒,就紧紧抓住李伟的手,急切地讲述他委屈的一生。
他说“下地狱(是)要坏人去的,我连人的称号都没有,他们都管我叫牛鬼蛇神,我到哪儿去呢”?李伟告诉他说全村的人包括领导,都知道你是好人,放心,一定会到非常美好的地方去。就这样张老师微笑着走了。
看着老人临终前释怀的微笑,李伟从中体会到了莫大的幸福,一个梦想就此悄悄地在他心里萌生出来。
1979年,李伟从农村返城回到北京,通过买卖邮票他淘到了第一桶金。1987年,李伟和几个朋友合作取得了民办医院的许可证,而当时批下来的却是开办一家综合性的医院,作为医院董事,在李伟的再三要求下,医院分给他三间病房六个床位,从此李伟也正式开始了他的临终关怀事业。
 鲁豫:您的第一个病人是谁?
鲁豫:您的第一个病人是谁?
李伟:我的一个邻居,四十二岁,是乳腺癌晚期了,扫描、化疗,特别痛苦。能借的钱都给花掉了,医生告诉她仍旧没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回家。她爱人每天照顾孩子,同时又要照顾他,整个家庭就要崩溃了似的。我跟她爱人讲,“到我们那儿去吧,她应该特别需要心理的关怀,多一点儿安慰”。接到我们病房,住了有四个多月吧,走的时候是微笑着走的,挺安详的。她爱人抱着她。这是我回北京以后的第一个病人。一年下来,一共有十七八个这样的临终病人。
鲁豫:这个病房在你们医院发展得顺利吗?
李伟:那个年代不管做什么都要有经济回报才行,到年底的时候,董事会跟我讲,“内科病房的肿瘤病人一个月差不多七八万上十万的费用,你呢?”事实上我一直在反对医院给病人做大量没有必要的检查,给他们使用很多昂贵的药品,其实真是一种浪费。
鲁豫:你们病房完全都不创收,是吧?
李伟:当时就是我的病房不创收,甚至还需要往里面贴很多的钱,大家就对我有点意见,劝我说你还是到内科吧。可是我又特别想办这样的关怀病房。
鲁豫:医院不支持,你们病房办起来不是就很难了吗?
李伟:很难。因为我坚持,最后院里面就不太合作了。比如说我开的处方到药房去领不出药来,或者一会儿没有这个,一会儿少那个,于是我也感觉到不能再在一起合作了。
事实上,一年之后这个“病房”就被关掉了。
和朋友的合作不得不终止之后,李伟仍然没有放弃办临终关怀医院的愿望。经过几番努力,1989年他再次找到了合作者。
李伟: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来我就跟部队的一家医院合作了。虽说是合作,但我一定要把我的这种服务理念注入到我的工作模式里面去,所以我谈的协议就是,我们共同使用医院的名称,但是我独立核算、自己管理,我使用一个三层楼的两千多平米,对外来说我们是一家医院,对内的实质就是一个租房协议。搬过去以后,我们想这些老人搬一次家非常难的,所以一下就签了三十年的协议。
然而,三十年的协议刚刚执行了三年,松堂医院就不得不面临再次搬家的危机。搬家,对于普通家庭和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麻烦又琐碎的事情;对于一个以临终病人为住院群体的医院来说,更是无法想象,无论病人还是家属都纷纷疑惑起来,这医院之前不都签了三十年的协议了么?
李伟:当时协议是一年十六万的房租,但三年之后,有人就提出给二十万、三十万要租这房,这种诱惑可能太大了,房东就开始让我们走,尽管协议没到期。
另外(病人的)家庭也提出一些建议,为什么不搬到城里、社区里面去呢,有这么多的老人集中的地方。综合各方面的原因,就开始搬了。真没想到搬的时候,社区的群众不让我们进入,不让我们下车,也不让我们(放)下病人。起码有上百个群众围在医院门口。好些人围在一起,有一个小伙子特别激昂地在给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抵制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搬进去了就轰不走了,这是一家死人医院,要搬进我们社区里头,天天死人,我们这辈子也发不了财了,多晦气啊。

老人与新的生命
鲁豫:这些老人就在街头这么一直待着?
李伟:我们车里七个老人就被搬到街区的小马路上了,这时是十一点多,等到快一点了,来了几个人,跟我们说必须明天十二点之前搬走,我们来检查,一个也不许有。我们真的挺着急的,后来就拨了一个民营医院的电话,他们说还有床,可以接待我们五个病人。在知道我们有几个特别危重的老人后,对方突然在电话里说了一句,你别忘了带押金呀,每个人五千块钱!我们才收每人两千块钱的住院押金,而且这些老人都已住了一两个月,都没有钱了。我想了想,北京还有一个能容纳这些老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四个小时前搬出来的那个楼。夜里两点多了,我开始打电话,给他们的领导打电话,最后同意说我可以搬回去,但房租要加一倍,三十万。我马上说,二十五万是可以的。最后他们和门卫打了招呼,让我们搬回去,然后就说从现在开始,每天一千块钱的滞纳金。我说可以。当时其实我真的没钱了,但也管不了那么多,我想总会借来的,总会筹到的,老人的生命是最要紧的。所以我们又连夜往回搬。每次搬家总有好人。
鲁豫:即使是第一次也碰到了好人吗?
李伟:夜里,一个的哥司机听到我们护士哭,听到我们突然碰到的困难,这个司机特别感动,说谁家没有老人?然后他就给我们一趟一趟地搬。都早晨九点多钟了,那个护士跟我说,院长你给他沏点茶叶水吧,那个司机特别好,帮咱们搬了四趟了。结果出来已经找不到那个司机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好司机的名字,但我从心里面会记他一辈子,这些老人会记他一辈子。
的确,无论是一些传统芥蒂的遗留还是各人从人生观到价值观的差异,对于生死,即便是现代社会中的很多人,也仍然不能以百分之百科学和理性的认识来看待和应对。生死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很多人总认为所谓“临终”的病人就都是老人。然而其实在松堂医院里,至少有百分之十的病人是中年人、青年人,甚至还有很小很小的小孩子。
松堂医院最小的患者是一个五个月大的女婴,送来的时候刚刚出生四天,只有两斤重。因为患早产儿综合症,刚刚来到人间的她,就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现在孩子已在医院的护理下,基本恢复了健康。然而她的父母却不知去向。

在医院录制节目的时候,还碰到过一个步履艰难的年轻人,他正处在二十一岁的花样年华。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有自己喜欢的偶像。然而因为先天性大脑发育不全,他终生都将这样艰难度过。
还有一位曾经在镜头中留下过美丽面容的年轻女子,只有三十七岁,如今依然美丽的脸庞足以窥见其年轻时的绰约芳姿,然而此时的她却已是宫颈癌晚期。
鲁豫:看到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我们面前慢慢消失,那是特别残酷的事情。现在医院里面有多少年轻的病人?
李伟:有十一个。我们常说黄泉路上无老少,我觉得尤其那些年轻人更需要社会的这种关爱。
鲁豫:现在年轻的病人里面哪些是让你觉得谈起来就会特别特别感慨的?
李伟:我有一个病人三十四岁,特别漂亮。三十一岁时得了乳腺癌,后来一直转移,没有办法最后到松堂医院来。我经常到房间里面去看她,每天早晨拿着小镜子化化淡妆什么的,嘴唇还抹一抹。我觉得她对自己生命的美丽是更珍爱了。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护士说,今天她不治疗,情绪特别不好,也不理我们,怎么也不配合。于是我就到她房间去了,突然发现她那个小镜子被摔在房间的角落里了,镜面全摔碎了。当时我觉得很反常,她怎么连最心爱的小镜子也摔碎了,我就坐在旁边跟她说话。我说了几句话,她可能觉得院长在,就把身子转过来了,她这一转过来我才看到是怎么回事。
待病人转过曾经美丽的面容,调整着自己的情绪让院长放心的时候,李伟才发现原来因为癌症的转移,她的面颊溃疡在逐步溃烂。而她刚住进松堂医院的时候面部仅仅是一个特别微小的溃疡,为了防止感染,护士天天拿敷料给她换药。被纱布和敷料遮盖住的创面使得病人一度忘记了这样的病创,淡忘了自己因绝症不断缩减的生命。然而经过一段时间,或许由于病情继续扩散的缘故,溃疡的面积不断加大,并未留心到这一变化的护士还按照以前的敷料和创面大小给她换药。当她像往常一样拿着小镜子照出了在显小的敷料后面未经掩盖的溃烂皮肤时,原本脆弱的神经再次回到了生命的边缘,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有一天会终结,但是她希望她的美丽永远延续着。面对病痛对自己美丽生命的冷酷蚕食,她再也无法忍受,将镜子狠狠地摔了下去……
李伟:我马上找护士长和护理部主任开了个会。我把这情况说了,一定给她换一个特别大的敷料,一定要盖住它,而且大家多去跟她聊聊天。过了一个星期就是她的生日,我们组织了会唱歌的护士围着她,大家给她过生日,唱生日歌。
这样被温暖和快乐包围着,仅仅过了二十多天,她走了。走的时候她是安详的,被温暖的生命完全没有呈现出被病痛折磨后的扭曲和狰狞,反而如同那面每天呈现在小镜子里的靓丽容颜。她真的是带着她的美丽离开的。
现在的松堂医院除李伟院长外,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加起来有百余人,床位有两百多个,其中护理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女孩子。女孩在一块都喜欢说说笑笑,喜欢漂亮,爱干净,所以一般的护理人员刚到这家医院的时候并不能很快适应。曾经就有一个女孩到了这家医院后因为极度地不习惯哭了三天。护理人员每天的工作特别繁忙,要给老人剪头发、刮胡子,帮老人换药,还要喂水喂饭,还经常握住老人的手给他们娓娓地讲些故事,每天帮他们剪花、或者剪那种绿色的树枝放在床头。医院要求她们能够让老人感受到那种亲人的皮肤的接触,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生命的那种热情和活力。
三十三岁的护工雍青和他的妻子李新荣来自四川农村,他们把孩子交给老家的父母抚养,一起在临终关怀医院工作,如今已经是第五年了。杨华是甘肃人,在这里做护工已经八年,是医院里资格最老的护工。经验丰富的她现在一个人要照顾六位老人。
高艳华现在是松堂医院的护士长。
高艳华:医院大概有八十多个护工。她们每天二十四小时和老人生活在一起,休息时间比较少,晚上几乎要两个小时起来一次。要是赶上躁动的老人呢,几乎这一夜就休息不好了。
李伟: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会有很多很多可能叫常人想象不到的要求,比如说有的老人突然就想他初恋的爱人现在在哪儿,叫我们去帮他找;还有的老人提出来,我们都九十岁了,难道男女还授受不亲呐,为什么不把我们放一个混合房间呢?我们总是尽量去满足他们的要求。
其实松堂医院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病人们互相交朋友,爷爷奶奶经常到房间里互相聊天。有一次护士长说,有几个奶奶老不回来,九点钟应该熄灯了,都九点半了叫她们还不回来。我去了一看爷爷奶奶聊得正高兴,聊北京四合院,聊他们家那个石榴树结了多少石榴,上头的砖雕是什么,因为我也是老北京嘛,我也跟他聊,聊着聊着,我就说哟,太晚了,明天咱们再聊。我就扶着奶奶说咱们回去吧。我扶着她们三个人正走的时候,突然一个奶奶就冲我说了一句,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还男女授受不亲呐?我马上就问这个奶奶,那你跟那爷爷在一个房间行吗?那奶奶特别坚决地说,我愿意!另外一个奶奶说她要是愿意我也愿意!第二天我就开会,跟大家说,咱们调查一下,特别愿意的,就给他们调一下。结果一共有十三个爷爷奶奶都特别愿意一起住,家属也说行。于是我们就把他们分到一个房间,其实异性真是有一种天生的引力,可能这种引力是终生的吧,他们在房间里特别融洽。聊天啊说笑的,心态也调整得很好,饭量也大了。调房后,一个老太太的女儿来找我说,“院长啊,我们家老头还在家呢,明天说来看她,老太太现在跟人家住一屋了,怎么办呀?”我说要不咱们给她分开?她说也没事,我们家老头也挺开放的。最后协商结果是老头来的时候分开,等老头走了再给她放回去。孤身老人也就无所谓了。不过有一个家属特别认真,来找我说,必须要分开!如果不分开,就到扫黄办公室举报!我一想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既然家属要求就给分开吧。可是那个爷爷奶奶有感情了,分开了特别想念。
鲁豫:就像以前那样串门呗。
李伟:可是老头儿被分开以后第七天就去世了,要不我想他还能活一段。
在松堂医院几乎所有的临终关怀病房里,都挂着漂亮可爱的儿童照片,旁边写有这样的字句:您相信灵魂不死吗?我们不会干扰您的思维的。
对于一些格外怕死的人,有时就要不忌讳谈死,让他们明确知道死的可能,免得他们怀抱恐惧,孤独地向死亡漩涡滑去。
在松堂思路清晰的老人为数不多,对待大多数的老人必须要像哄孩子。哄,是这里工作人员工作的核心。
鲁豫:跟老人在一块得哄他们是吧?
高艳华:对,跟小孩一样,老小孩。
鲁豫:好哄吗?
高艳华:不太好哄。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可以吓唬吓唬,这些老人你不能吓唬,既尊重他又要哄着他。
鲁豫:听说在你们医院里面是白天特别安静,到了晚上特别热闹?
李伟:有这种情况。有个老人晚上自己一定要起来,说要到公主坟下车。我们就推着轮椅转了一圈,说“公主坟到了”,就回去了,我们就是幼儿园大班。
鲁豫:他每天都要去公主坟吗?
 |
松堂医院的创办人李伟 |
鲁豫:护士长肯定也照顾过这样的病人吧,你都怎么哄他们呢?
高艳华:董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军人,吹乐曲的。他们家住四层楼,有上下夜班的,只要楼道里一有声音他就开始骂;把一栋楼的大人小孩吵得都不得安宁,所以这个楼层里边的人都希望他搬出去。后来送到我们医院,到医院的第二天他就开始闹腾。晚上楼道里有护士或是护工起来为老人倒尿或者查房,他一听着声音就喊、骂,拿个挠痒痒的小耙子敲病房里的氧气管道。他嗓门特别高,连着几个晚上怎么哄都不行,他同房还是个有心脏病的老人。护士去了他打护士,还打护理员。最可怕的是拿一个尿壶,接了半壶尿到处洒。
李伟:她说的这个董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连长、营长、团级干部,管别人管习惯了,而且又曾是一个乐队的音乐指挥。可能退休以后,社会把他淡忘了,而他需要得到社会的这种认可。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以后,组织全院病人,发选票,说这个老领导过去是乐队指挥,让他当我们的厅长吧。大家都选他当厅长,从这以后他不但不打人,谁要声音大点,有什么不礼貌,他就去管,说话声音轻着呢。
鲁豫:我听说有一个病人一到晚上就躲在楼道里面啪啪打枪,您得跟着他啪啪也打几枪他才能睡觉。
李伟:有一个爷爷当年打过仗,他对丛林里面的印象特别深,有时候他晚上突然起来藏在角落里,嗒嗒地打几枪。我说“你干吗呢”,“有敌人”,他特别认真地说,后来我也跟着他,说那个角落有敌人,嘀嘀嘀嗒嗒嗒,打完了,我说都消灭了,咱们该睡觉了,他就特别高兴。
鲁豫:每天晚上都要这样?
李伟:也不是每天,反正一个月得有两三回。
对于处在临终期的老人们来说,心理上的关怀远远比医疗上的护理更重要。在生命末期的老人,更需要被尊重,他们有着与所有的人一样的需求,他们需要参与社会并被社会认可。也正因此,不能过早地把老人放在四面水泥墙里,把他禁闭起来,等待他生命的终结。这样等待死亡显然是不和谐的。
在松堂医院,几乎每天都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陪老人们聊天。志愿者来到的日子往往是老人们最开心的时候,死亡的阴影在这一刻被冲淡了。
李菊英老人今年九十岁,从小随父母居住在日本。慈眉善目的她是志愿者们最喜欢的老奶奶。
李菊英:我最喜欢志愿者到我们房间来和我聊天。志愿者是现在青年里思想最好的人,有这么多的好青年,我们国家的前途会越来越好。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张大诺今年三十六岁,是北京一家报社的编辑。他从2003年的夏天开始在松堂医院做志愿者,因为工作的机动性,每个星期他都会从石景山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来探望老人。他所能做的仅仅是陪着老人们聊聊天,性情温和的他是这里的老人们最喜欢的志愿者之星,而他却只是松堂医院近十万人次的志愿者中的一个。
鲁豫:怎么开始到这来做志愿工作的?
张大诺:我之前也做过临终关怀,那时候是叫城市贫困癌症晚期病人,后来到北京之后呢,我一直想继续做这个工作。
鲁豫:本来是在哪儿做?
张大诺:在哈尔滨。北京松堂医院比较有名,我就找了过来。他们对志愿者非常开放,只要你来了就说明你是有心的,登记之后看哪门开着就随便进吧。
鲁豫:你谈的第一个病人是谁?
张大诺:张奶奶,当时她穿戴非常整齐,中午没有睡觉,坐在病房里头。她可能是很孤独,门口过去一个人就非常好奇。我过去之后又回来了,发现她正盯着门口。然后她冲我招手,我进去之后蹲门口跟她聊天,聊了几句之后她突然间跟我说起英语,什么what’s your name,How are you就这样的,那我就继续跟她说英语。事后我才分析出来,她当时以为我是向她求教英语的一个学生,由这个作为开端,我俩就慢慢建立了联系。
大概有两个月吧,我每周去看她一次。那天去看她的时候她正睡觉,我就站旁边。她突然醒了,看见我之后突然间啪啪打我,说“你怎么才来,我都想死你了”。我当时挺惊讶的。然后她爬起来,指着窗户外边过街天桥说,我就盯着那个桥,心想下雨的时候你肯定不能来,不下雨的时候你应该能来。然后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对我哭。当时我就觉得,其实她们是这么一群有着非常丰富感情的老人。虽然她有时候连自己的年龄都记不住,从那以后我跟她们有了这种情感的沟通,就经常去看她们。
有一个老人去世以后,他的四个子女一起给院长写了封信,说看到我们的父亲能够走得这么安详,我们心里面觉得很安慰,也特别感激。或许这样一封信,也说明了一个变化。十九年,对人、对医院、对社会来讲,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松堂医院来说,或许今日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很多人已经接受了临终感怀这个概念,也接受了松堂临终关怀医院,认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贡献。
2003年3月,松堂医院面临他们建院以来的第七次搬家。从十九年前的六张病床发展到如今能收治近两百名病人的松堂医院,从曾被人撵出大门到今天全社会的关注,从当年的风华正茂到今日已两鬓斑白,李伟的人生伴着他的临终关怀事业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从1992年到2003年这十一年里,他领着一百多位病况危急的老人辗转于北京城的西北东南,一共搬家七次。第一次搬家时被人撵出使他痛心,而第七次搬家则使他看到了希望,欣慰不已。
鲁豫:前后七次搬家。第一次搬家是那样的惨痛,但最后一次搬家让人觉得很欣慰,让您觉得非常欣慰。最后一次搬家,是2003年2月26号对么?
李伟:这次搬家和以往不同。当知道我们又要搬家了,好多的志愿者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到医院来说一定要帮助我们搬家。各个学校的差不多有五六百个志愿者要参加我们的搬家活动,每一个老人能平(均)到五六个人来帮助他;北京的那些出租司机们也有一百多人,他们都说我们那天不拉活了,早早来到医院,几十辆出租车全来了,他们都义务地去帮助老人;那些999急救中心的,还有国外的朋友都来帮助我们。这次搬家真是心里暖洋洋的,全社会那么理解我们,那么支持我们。从早晨不到六点就有好多人来了,帮助我们去整理,帮助往车上抬,甚至于我们出来的时候警察都帮助我们疏导交通,因为是几十辆上百辆车横跨北京的一次大迁徙嘛,路上的交 通警察都帮我们维持秩序,特别好。真的,通过我们十多年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大家都在支持我们的工作,我想我们今后再也不用搬家了。
通警察都帮我们维持秩序,特别好。真的,通过我们十多年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大家都在支持我们的工作,我想我们今后再也不用搬家了。
鲁豫:肯定不会搬家了,现在你们住的地方不是租的了,是你们自己的房子了。是吗?
李伟:对,我们买下来了。
鲁豫:老人们就有一个永远的家了,真好。新的一年您自己有什么希望?对松堂医院有什么希望?
李伟:希望我们把老人照顾得更好。好像别人都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我理想不太远大,我就想到明年我还能好好照顾老人,后年还照顾。
鲁豫:谢谢院长。院长特别幸福,最近要去温哥华,去看太太和孩子,跟家里人在一块待一段时间。医院搬了第七次家以后,再也不用搬家,他们医院有了自己的院址。也希望在这个医院里面,院长跟医护人员,还有老人们都能够好好的,希望这些可爱的老人们能够健康,过得幸福。
(摘自《面孔――鲁豫有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7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