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她说她没弄错,信皮上是写着我的名字。由于是头号文化首长来鸿,她不敢耽搁,让我马上去作协,并强调这是党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记不起当天我正给哪家刊物写小说了,但我记得小说正好写到了收尾,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即将完成作品的最后几笔,是最难以割舍的。于是我和王淑珍商量道:“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协,我手头这篇东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她说:“那可不太合适,你考虑一下吧!”
“这么办吧。”我想出一条折衷的方案,“你要是真没张冠李戴,你现在就打开它,给我念念信中内容如何?”
她开始说不合适。但我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是批评我虚心接受,我不怕公开亮丑。几经磨合,她终于按我的意见办了。她告诉我,她粗粗地翻看了一遍,不是批判你的文字;是乔木老人读了你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之后,写来的阅读感受;但是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五页信纸,里边还有涂抹之处,因而无法读给我听,还是等我去作协之后,自己来解读这封长信吧。
电话挂了。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正好,第二天是作协开会的日子,我去了作协,便与友人刘绍棠一块恭读了乔木同志的来鸿。信文如下:
维熙同志:
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为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到在刊载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改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叙事本领,你的文字也很讲究。不过文中仍有些细微的疵点。由于积习,我边看边作了一些记号。现在依次写给你,一来供你参考,二来也算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点报答……
以下,乔木同志按页码顺序,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那般认真,写下了若干条文字、标点和语法上的失准。
读罢来信,我和刘绍棠都笑了起来。无论如何我们也想象不到,乔木同志在养病时会拿出这么多时间,为这篇小说的文字号脉,读一篇与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长达六万多字的小说,并写来这么长的一封来信。我俩估算了一下,不算阅读作品时的圈圈点点,仅仅这封匡正我小说文字的信函,怕是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真是令我们后来人感动不已。
绍棠问我:“你觉得这位大秀才,给你开出的‘药方’怎么样?”
我回答说:“有的一矢中的,有的我还得好好消化一下。”
绍棠率真地说:“老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过,中国语言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湖水,而是不断流动的大河,它也在时代变革中变化和发展。……不管怎么说,老人这么大力气,给你写来这封长信,说明一个问题,小说感动了他。”
我说:“老人是在养病中写来的,我只有感谢老人的分儿,我要尽快给乔木写一封回信。”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复信还没有写出,第三天下午我又接到作协的电话,说是乔木的秘书又送来一封信,让我及时到作协来一下。这次我没理由耽搁,因为一篇不成样子的中篇小说,已然让老人花费不少的心思了,老人再次来信,我理应立刻去拆封老人的手书。记得,赶到作协时已近下班时间,作协秘书长宋正要下班,他把信递给我后对我开玩笑说:“看样子,意识形态口的旗手胡乔木,是盯上你了,三天内两封手书,算是开了文坛之先河。”我说:“老宋,万一小说引发了什么麻烦,你这秘书长还得替我扛着点。”他为解疑地说:“你真是傻瓜,要是找麻烦的话,老人会把信直接写给你吗,那会自上而下地交市委宣传部,再由宣传部下达到北京作协来的。这个书信程序,就说明乔木老人对你的文学创作关爱有加!”
信拆开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除了几句简短的文字之外,老人竟然用笔画来两幅凌乱的几何图形。乔木老人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维熙同志:
昨信发后,想到信中对垂直线的解释仍不正确,因为一条直线(或平面)相交成直角时,这条直线就是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的垂线和垂直线(见现代汉语辞典152页垂直线),这另一条垂直线并不需要是水平线……
信的中间部分,是乔木老人用笔绘下的两幅垂直线的几何图形(笔者从略),信尾直白了他写此信的用意:
……我的信和你的小说,同样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设想,因而对垂直线作违反几何学定义和错误的解释。特此更正。
胡乔木 二月十八日
看完此信后,我顿时明白了乔木老人的用心。但老宋却像是坠入十里迷雾之中。他说:“不是评你的小说吗,怎么论证开垂直线了?”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一个人物引发的。小说中有个劳改右派名叫范汉儒,他是个屈原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劳改生活中,对一切都一丝不苟,因为在困境中活得依然挺拔,因而得了个“六点钟”的绰号。因为六点钟时,时针与分针成一条垂直线。乔木同志就是为我小说这个人物绰号,画来的几何图形,似在证明六点钟时针与分针上下垂直为“1”,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垂直。
老宋哈哈大笑:“我还是第一次领略老人的认真。”
我说:“我回家得赶快给老人写封复信,不然真的对不起人家一片心了。”
……
我复信是二月二十二号写完后寄出的。这封复信我很花心思,因为面对当时的文学艺术,我有话要说;而乔木同志又是意识形态口的主管人之一,对他说说我的文艺观,也许比与中宣部长对话还要直截了当。记得,我在信中主要阐述的主题是,我们文艺界的领导,太偏重文艺的宣传作用,因而很少涉猎文艺自身的生命价值;由于太看重歌颂胜利的功利作用,而很少在作品中描写失败,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我在信中列举了苏联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时电视台在播放这部电影),之所以流传至今并在播放它时让北京万人空巷,更大程度上在于它自身的艺术张力和作品的血色真实。而我们的文艺导向太热衷于歌舞升平的作品,这虽然能满足于一时之需,却难以流传于永久……记得,我这封信写得很长,其用心在于让文学艺术从单一的颂歌中走出来,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全貌――包括对建国之后的反右――直到血色斑斑的“文革”,都应在文艺的视野之内,以利于民族自识自省。当我把信函投入信箱的瞬间,曾产生过片刻的犹豫,我生怕这样一封复信,刺伤了老人的心。但我自问无愧于心,最后还是将信投进了邮箱。归来之后,我又感觉只有这封抒怀的信函,还不上老人为我付出的时间和心血,过了几天我又匆匆包扎好我新出版的两本书(长篇小说《北国草》和劳改队纪事《燃烧的记忆》),再次去邮局,寄交给了乔木同志。
两三个月过去了,没接到乔木同志的信函,我认为我们之间的书信缘分到此为止了。第一,他是个大忙人,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似并不过分;第二,我那封复信写得非常直率,也有可能引起老人的不快。谁知道呢?直到该年的六月下旬的一天的下午,作协派司机给我送来印有乔木办公室字样的信函。打开看来,信是其秘书邱德新的手书。全文如下:
维熙同志:
我是胡乔木同志的秘书,今天乔木同志让我来看看你,祝贺你的新作问世,同时让我谢谢你送给他的书。
你说到前次已经给乔木同志写过回信,但我们没有收到,现在正在查找,估计能找到。你如能把发信的时间告诉我们更好。送来中央广播电台关于听众对《北国草》广播的反映,乔木同志特告穆之、文涛同志读。一并转告。
祝你取得更大的成绩!(附乔木办公室电话号码)
邱德新
6月22日上午11时
至此,我才明白乔木只收到了我的赠书,而没收到我的复信。我立刻按照信上乔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邱德新同志打去了电话,告知其我回复乔木同志信的准确日期。事后,从乔木的来信中得知,我那封复信他还是没有收到。老人于同年的七月中旬,又将一信送至作协,同时还附有我赠他的长篇小说《北国草》:
维熙同志:
非常遗憾,你给我的回信被秘书丢失了,不知混在什么文件里,现在还没找出来。
承赠《燃烧的记忆》和《北国草》二书,谢谢。《北国草》已看完,我在看时对文字的错误和毛病,仍随手作了记号或改正,这些不一定都对,现暂送还供你再版时的修改参考,你看后仍寄还我。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书,所以它的广播能得到那样广泛热烈的反应。我和很多听众一样,希望它能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听众反映已转到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使它能在教育这一代青年发挥作用。对于整部小说,我现在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评价,因为没有充分的思考。我手头还有做不完的一些困难工作,所以虽很想找个时间同你相见,暂时却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会有的。
祝你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
胡乔木 七月十五日
读过乔木信后,我打开老人读过的《北国草》。许多书页折着边角,凡是折角的地方,必有乔木的圈圈点点,其中有些地方,还留下他改过的文字。我当真为老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感动了。这是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他要花多大的力气,读完并校订完这部长卷?此时乔木已是年近八十高龄的古稀老人了,还能为一部小说字斟句酌地圈圈点点,真是够难为老人的了。想到这些,我真是后悔不该把一部冗长的小说赠给乔木了。但是一个作家,当时何以回报乔木同志对《雪落黄河静无声》投入的精力呢?再看看他的手书中,那些歪歪斜斜的字体,说明老人写字时的手在颤抖。据乔木同志秘书邱德新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老人是在医院养病时读完的《北国草》,那书上留下的圈点的文字和那封来信,也是在医院病榻前完成的。怎么办?我曾产生主动去看望一下老人的意念,只要和其秘书通个电话约个时间,此心愿就能了却;但多年劳改生活,养成我惧见上层的习惯,最后还是决定将对感谢老人之情,深埋进了我的心底。直到1985年的初春三月,乔木再一次派秘书给我送来一信,信是3月1日落墨的,老人在信中告诉我一个喜讯,他已然找到了我的那封复信,是秘书将其压在文件堆中,后来将其锁入保险柜中了。老人说他已经读了我一年前的复信,但不能现在就给我答复,因为他刚刚结束了三个月的南方之行,回京后有一堆事情等待他处理。信尾老人特意附上了他家的地址:南长街×××号,有信让我直接寄到他夫人谷羽处,以防再次发生耽搁。
此时,我已离开了北京作协,到了中国作协工作了。虽然我工作很忙,但老人圈点我作品的这份情义,我始终牢记于心。当时间到了1986年的秋天,作协在西苑宾馆召开理事会的晚宴上,我第一次与乔木同志见面了。当时老人坐在主桌上,我与李国文、邓友梅两个同辈友人,端着酒杯去向乔木敬酒。至此,我才算有机会表达了我对乔木的敬意。我说:“您给我的五六封信,我都很好地保留起来了。您这么大的年纪,工作又那么忙,还抽出时间为我不及格的小说号脉订正文字,为我的创作加薪助燃,我感激良深。过去没有机会见到您,今天让我敬您一杯酒吧!”乔木喝酒了没有,今天我已无准确记忆;但我准确地记住了,他盈满双眼的泪水;还有我们握手时,他那只不断颤抖的手……
乔木老人在1992年9月18日他八十一岁时,走完了他人生之路的全程。由于与乔木同志没有接触,我无法写出一个完整的胡乔木,更无能判断文化界对胡乔木的多种褒贬之词的是与非;我只想从这几封手书落墨,勾勒一下新时期以来他与作家的关系。据笔者所知,历史的新时期前夜的1978年,胡乔木亲自去上海,把工人作家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引领到北京给正待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代表演出。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的文字起草人,会前会后其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老人还是让代表们在会前“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充分表现了他关注文化的细心和开创历史新时期全新局面的睿智。到了历史新时期之初的1982年,文坛曾有人要批判王蒙以意识流手法写出的小说,在“兵临城下”的时候,是胡乔木为之解危的。如果说以上的文字追述,都是流水般平静的话,乔木也有过不平静的遭遇:有一次,他在去南方考察工作时,竟然想去见见厦门鼓浪屿新生代的女诗人舒婷。这是老人礼贤下士之举,但天性坦荡的舒婷,并不想与这位意识形态口的总管见面叙谈。无奈之际,舒婷拿出了主动出击的姿态,到乔木下榻住处,主动去看望了胡乔木老人。但是让她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胡乔木还是到她家里来了。当天,她和他的先生――厦门大学教授,在与乔木交谈学术问题时,因有些意见不同,而发生了一些争执。按说,在学术范畴内这是属于正常的,但因其争执的声音很高,惊动了担任乔木警卫的当地公安局长,因而其交谈结局无果而终。据舒婷事后告诉我,她对老人的印象是:老人是懂得文学的,但由于多年为官沉积于心的那个罗盘指针,总是在惯性中运动,因而交谈无果而终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情。她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乔木老人,对我给他的回信中提及的问题,始终没有片言的回复一样――属于他难于回答的问题。虽然如此,还是让舒婷感悟到“老人姿态很高,并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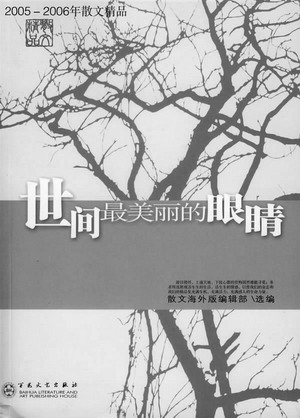 有因为发生冲撞的火花,而像有的文化官员那样,找作家创作上的麻烦”。胡乔木何许人也?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与作家相处中,还是显示出来一定程度的宽容。不能小看了这个人文细节,因为许多才疏学浅的文化官员,对有异议的文化人,轻者进行开导训斥,重者进行整肃。在这一点上,乔木老人是不是接受了过去的历史教训?他在鼓浪屿与舒婷会见留下的这段往事,给后人留下了思索的话题。他一生的命运也曾几度沉浮,也曾留下身不由己时的一些人文缺憾,但其关注中华文化的兴衰始终如一,这又是留给后人的一段文史佳话。
有因为发生冲撞的火花,而像有的文化官员那样,找作家创作上的麻烦”。胡乔木何许人也?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与作家相处中,还是显示出来一定程度的宽容。不能小看了这个人文细节,因为许多才疏学浅的文化官员,对有异议的文化人,轻者进行开导训斥,重者进行整肃。在这一点上,乔木老人是不是接受了过去的历史教训?他在鼓浪屿与舒婷会见留下的这段往事,给后人留下了思索的话题。他一生的命运也曾几度沉浮,也曾留下身不由己时的一些人文缺憾,但其关注中华文化的兴衰始终如一,这又是留给后人的一段文史佳话。
以此为尺,丈量一下时下一些文官的长短,便能知其“胖瘦”了。君不见时下一些胸无多少墨汁亦不读作品、只靠听下层汇报、便颐指气使地对作品进行褒奖和封杀的文官吗?对比之下,乔木可以算是一面供文官自照的明镜了!岁首春初,写此文海钩沉的忆旧文章,既是对辞世十三年乔木之魂一纸迟到的祭文,也可以视为一个文人,对今天文苑清风的期待……
(摘自《世间最美丽的眼睛》,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4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