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号上午,我爬到纪念碑的浮雕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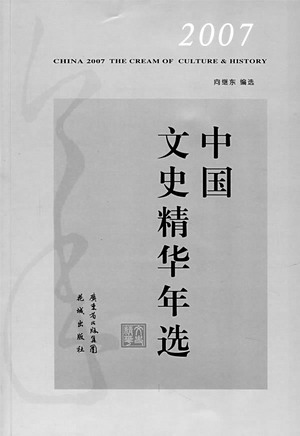 我上班,必在广场边上的南长街由1路换乘5路。从3月底至4月初,早上在广场上转一圈,下班后更是在广场的花圈丛林中转悠呢。按说清明节前后的悼念,尤其
我上班,必在广场边上的南长街由1路换乘5路。从3月底至4月初,早上在广场上转一圈,下班后更是在广场的花圈丛林中转悠呢。按说清明节前后的悼念,尤其
更有不同层次的演讲。谁都可以找个高处如台阶、灯竿架爬上去,或即兴成章,或照纸喊念。但往往直接的、口号式的宣讲能博得大家起哄般的欢呼。一般下午到天黑最热闹(大多人提前下班都来此“加班”)。表面主题都是悼念周总理,而深意则有人们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对一小撮人(当时“四人帮”一词还不流行)的愤慨。有趣的是,你以为你是来看戏的,但你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也被触动,于是也大声抱怨了几句,没想到旁边的人们让你再讲讲,于是你怒口再张,也成了这千百出戏中的一个角儿。
我敢说这些广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来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的关系极远极远――对自身生活的极度不满才使许多人把怨忿发泄在领导层的坏人身上,把忧伤洒在对一个故人的悼念上。而我也通过个别人的演讲、少数人的诗词确实看到了民主精英、文学精英的潜在。
4月5日6点多我又在长安街换车,一夜之间,广场的几万个花圈荡然无存,连柏丛上扎的小花也点滴不见,纪念碑上干净冷清,碑周围围了一层工人民兵和两层士兵。人们传递消息:昨夜动用了公安和工人民兵在一线(广场)清场,运走所有花圈,驱赶所有群众并抓走一些人,军人作为二线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中待命后援;大部分花圈拉到郊外烧了,少部分花圈可能在人大会堂的地下室里,被抓的人关在旁边的红楼中。不少人质问警戒的军人甚至讽骂他们,对方不语,只是挽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纪念碑。
我决定今天上班迟到一两个小时。大约晨7点多,一队中学生扛一个普通的花圈近前却被阻住。群众开始起哄、呼喊、冲挤,军人的人墙一下就破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那个唯一的花圈拥上了纪念碑的台阶。我看见那些士兵,整好队撤向小楼方向。
那花圈很普通,摆在浮雕前很不夺目。有一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的平台距地面有两三米高,根本举不上去。我就用攀岩的动作,连勾扒带悬体援撑,爬到了浮雕顶的平台,又哈腰接住底下人递上的花圈(好像也有别人爬到了上面)。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呼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便衣拍下来了。
有人又开始在纪念碑的基台上演讲,口吻猛于以前,但仍没有直点人名。这时有一个着便服者很强硬地干涉,大概说了:清理花圈是市委的指示;清明节是鬼节,要反迷信;你们受了坏人的骗;马上离开。这人30岁左右,面目端正,他左右还有几个人跟护着。人群中有人喊:打丫的。于是真有人揪打他,但都没有下狠手,他被随从护着撤出了纪念碑。
我觉得我该去上班了。这几天工厂盯得也紧,一律不准请假,晚去一两个小时工友还能替我跟领导搪塞。再就是我刚才在纪念碑半腰上“亮相”也太过分了。可是我真舍不得走呵,好戏才开场,哥们刚刚进入角色,加上好胜心又敦促我:你就想当逃兵么,跌份。侥幸心理提醒我:被抓哪就那么轻易轮到你。这早我穿的是一件劳动布的干净工作服,很肥的制服裤,高腰白回力球鞋。就算他们拍到了我,但我若去换一件衣服再潜出广场并且不再出风头而纯是看热闹不就安全了吗。我决定去虎坊桥一带的工友张××家乔装一下。
我离开广场换了外衣又返回
在虎坊桥的工友张××家换上一件浅灰的夹克时,我对刚才攀爬纪念碑放置花圈的行为略后怕,并决心再返广场后只当看官、绝不当角儿。可我一来到天安门广场,肾上腺素又活跃了。凑近纪念碑,就有人认出我:都在找你呢,你干嘛去了――嘿,你换了件衣服。我说:刚去吃早点了(的确吃了)。我又和刚才几个爱挑头的汇在一起,望着激动的人群我脑子一热,就高呼口号,大概有:打倒法西斯、悼念总理无罪、人民万岁、镇压群众没有好下场。有人喊:唱《国际歌》吧。我起了头。我头一次起这个歌的头,自己的血先小沸起来。又有人喊:让我们走向天安门。反正稀里糊涂,我成了第一排中的人。
开始第一排很宽,至少有二三十人,后越走越窄――可能有人忌讳前面老有人给我们拍照。快走到国旗时,第一排仅剩十几个人。我们的前面总是有黑洞洞的镜头,就算那镜头变成枪口又怎么样啦,让你们开枪吧。当时我心里疯疯狂狂,必死的决心油然天降。
可就快接近国旗时,《国际歌》唱完了。因为没有公安和民兵阻拦我们――没有反作用力也就没有作用力,因为我们也不知要到国旗下干嘛――可能集体意识忽然空白了。我们几排人尤其是第一排的人还没等尴尬太大,忽听有人喊:我们去大会堂找花圈去。于是我们别别扭扭就散了队形,又一哄地奔向人民大会堂的东门。
这天广场上人少多了,也因各单位紧急传达不许职工去天安门广场。昨天(4月4日)广场同时估计有百万人,总人次达到二百万,花圈就有三万多。广场上各种消息仍在蜚传,什么邓小平昨天也来广场了,什么昨晚清场也是老华(华国锋,当时国务院代总理)的主意,他说坏人跳出来了;什么吴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说天安门的广场发生的事情是邓小平准备好的反革命事情。在中国,不少上层领导的新动态,有时一夜就能传入市井。
我随着人群拥向了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半地下室门口(在台阶以北),但被层层士兵人墙阻住。士兵手无寸铁,却挽起臂膀,死命抵挡着人群拱动式的冲击。人群中乱喊着口号,也有骂语。士兵们啥也不说,有当官的说这里真的没有花圈。人群是有些像乌合之众,至少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有一个中年人(估计不是对方的人)因说不应冲击大会堂便被几个人拳打脚踢,直到他喊冤我也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才得以摆脱。打他的人一看就是胡同串子(小痞子)。
在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
这时候××(后来的谈判代表)掏出了一首诗,又将手提喇叭递给我,我就念了这首二三十行的《告工农子弟兵》(这诗可能他昨在广场上念过)。诗的大意是:工农子弟兵,请你们倾耳听,你们吃的穿的都来自工农,你们的枪口不应对着工农(当时士兵均赤手空拳,除几个礼仪式的门卫),你们应分清敌我。这诗节奏、用词、韵脚都不讲究,比这几天天安门诗抄的优秀者逊色不少。但它的效果好,激起人群欢呼并加大了对士兵的起哄。由于用力抵挡人群的冲拱,大多战士的脸都有汗水,他们的胳膊互相挽得死死,估计也是在执行命令:誓死保卫大会堂,一定不能让坏人冲进来。而群众的行为肯定不是在执行什么命令,也没有什么组织,胡乱有个什么说法,就会一呼百应。比如,又有人喊了一嗓子:花圈都藏在历史博物馆里。于是人群呼啦啦地就退下了人民大会堂台阶,拥向历史博物馆的西门。
人群上到了门前的台阶,这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出来干涉,一个女同志大喊:同志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里面都是国家财产,都是重要的文物,里面没有花圈,你们冲进去只能使国家遭受损失。那个女同志的确义正词严,人群竟不再往前冲了,却步了,后退了。也因为有人喊:走,我们去小红楼,那里有我们被抓的战友和花圈。
嗷,嗷,人群躁动着呼喊着往历史博物馆西侧偏南的小红楼拥去。当时都知道,那小红楼是军、警、民兵三方一体的联合指挥部。广场上的小道消息早就传出: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也常来这坐镇;首都工人民兵的总头叫马小六;(甚至说)王洪文几天前也来这视察过,并且江青、张春桥经常在人民大会堂的平台顶观望广场的动静。
我觉得我差不多该走了,好歹下午在厂里露个面,否则算旷工就麻烦了。可是不知不觉,并且人群好像都跟着我们呀。反正我不可能说:我该去上班了,小楼我不去了。我自知小楼是最不应该冲的,那是武装力量的司令部,里面可不是吃素的。
可我一半由于被裹挟一半由于自尊(临阵脱逃太跌份了),还是被人群簇拥到了小红楼前。
在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1976年4月5号的中午,广场上的部分群众都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所三层红砖楼前。楼门前,围了至少三层士兵,均未佩武器。士兵们手挽着手,抵挡着潮涌般的人群。
士兵的后面有当官的用手提喇叭不停地解释和警告:小楼里没有花圈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不要受坏人挑唆冲击营房;请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再往前冲后果要自己负责。但人群只有一句回语: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也有人喊:人就是被抓到你们这里的,花圈也藏在这里。军人的喇叭和人群的声音一直在对喊,并且人群对士兵身体围墙的拱劲正逐步加大。
人群里也有人喊:大家不要乱,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派代表跟他们谈判。于是人群一遍遍地齐喊:我们要谈判!我们要谈判!的确人群里有个别人,故意使劲冲撞战士,而战士仍是手挽手地不松人墙,也不说话。
没想到,过了10多分钟,对方竟同意谈判了,还让我们选出五人作为谈判代表。我因站在前列,加上个头也高(像是会打架),并且刚才在人民大会堂前、纪念碑前多有领呼口号、宣诵诗歌(《告工农子弟兵》)等出风头举止,也被选为了谈判代表。
进小楼前我们五个也没分工,也没合议,仓促上阵。进小楼前,有人喊:一个小时你们不出来,我们就冲。
除小楼外的几层士兵人墙,没想到小楼大门的过道里也塞满了士兵。根本挤不进去。也不知谁喊:从上面过去。我们五人就爬上了士兵们的肩膀,爬了好几米长的“肩膀走廊”后才脚着地。小楼里没什么特殊,除了军人就是穿便衣的人。广场上的人群大都知道,这几天在广场上被抓的群众有不少都是被扭送到这里的。
我们上到了二层,被引进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我们好像都不会谈判,暂时也不知跟谁说,那就先喊着一成不变的口号: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口渴,又加喊了一句:给我拿水来喝!几个战士立刻用搪瓷缸去接了几缸子的凉开水。我们一饮而尽,跟补喝“临行喝妈一碗酒”似的。
一会进来一位高大的没戴领章帽徽穿绿军衣的人,面不丑,约40多岁。有军人介绍:这是我们的首长,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谈(好像有军人称他×师长)。这位军人口气和缓,措辞不卑不亢,大概说了:你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们不要受坏人挑唆上坏人的当;花圈不在这小楼,我不知道在哪儿;我们抓的只是极个别的坏人,他们也没有关在这里,关在哪儿我不知道;你们应劝广大群众退回去,离开广场,回到工作岗位。因为我们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这位首长也不得不重复了好几遍他的话。
大约谈了20多分钟,楼下传来更强的群众呼声,有一句的意思是要我们到窗口来。估计是想知道谈判结果以及我们是否都被铐起来了。我们来到窗口,有人向窗外的人群呼喊:我们很安全,他们耍赖,说不知花圈和战友在哪,你们别着急,我们要跟他们继续谈。
继续谈,没什么新鲜,加上窗外人群高喊着让我们回去。我们稀里糊涂地下到一楼又爬过众战士的肩膀,回到人群中,并告诉大家:他们拒不交出花圈和我们的战友,谈判失败。人群中有人说:你们回来了就好,我们担心你们五人也会被扣起来。当时广场中央有广播车(上海小轿、顶四个喇叭)被人群围住,更多的人向那里蜂拥,我们谈判小组就散了。
下午烧汽车时我已溜走
这时广场上的焦点转到了国旗南侧的广播车那儿。那辆小车内有一个女的广播员。人群围拥着那车使之不能动弹,有人开始用手拍打车厢和玻璃。也有人喊:把广播车掀了。
我觉得大势不好,着实该闹事了,我是该撤了。就算我干了反革命的事,我也不愿当“反革命分子”。我来广场,本是想凑凑热闹(当然基本的正义感是有的)后来发展到出出风头、泄泄青春之火,绝没想着“以鸡蛋碰石头精神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
大概15点多,我悄悄进了车间,赶紧换了工作服。
我们厂里是16点40分下班。一小时后我又来到广场。见人群不如白天多了,而成队的民兵已集结在广场四周。我又听说了我下午离开广场后的事情:把政府的广播车掀翻了,还烧那汽车的轮子;联合指挥部小楼那边也有人纵火,后被战士扑灭;没有什么太大的暴力事情。广场上的人有不少正撤出广场,到处都有声音在传播:今晚他们(指当局)肯定会动手。
4月6号上午我直接去的工厂,所有人都在议论昨晚广场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信息大致是:傍晚6点多,广场上的所有喇叭广播北京市长吴德的讲话,主要内容是现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搞反革命活动,广大群众应该迅速离开;晚上9点多,广场上的灯光全部亮起,成千上万的工人民兵和警察以木棍和皮鞋殴打留在广场上的群众,并抓走几百人;卫戍区的部队都呆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待命;昨夜在广场以外也抓走了一些“闹事者”(几年后看到资料说:当天江青、张春桥等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广场事态;6点30分广播吴德的讲话;动用一万多民兵、三千警察;在广场抓走388人;五个营的军人在广场附近待命)。
1976年4月7日,电台和报纸传来惊人的消息: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对暴乱分子采取了无产阶级革命措施;这场事件的后台是邓小平(这可真冤枉或者说高抬老邓了);中央形成决议,撤消邓的党内党外一切职务;准备清查参加暴乱的反革命分子。
定性“暴乱”让我没想到;“四五事件”连累了邓小平我觉得很遗憾。4月7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清理广场的民兵、公安代表,说是表彰他们粉碎了反革命暴乱。4月8日《人民日报》有文章《天安门事件说明什么》,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并号召全党全国继续批邓。
(摘自《2007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3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