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末的一天,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来电话。这个电话后来成了帕斯捷尔纳克无法解开的一个心结,始终困扰着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日瓦戈医生》蜚声世界的俄罗斯诗人、作家。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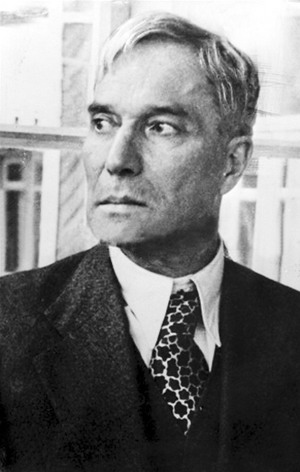 |
|
帕斯捷尔纳克 |
5月13日深夜,曼德尔施塔姆因“反诗”被克格勃逮捕。这首克格勃在诗人家中搜查了一夜也未找到诗稿的“反诗”,现以审讯记录的形式保存在克格勃档案馆中――
问:你意识到自己创作反革命的作品是有罪的吗?
答:我是下面这首反革命诗的作者:
我们未感到生活有国家作为脊梁,
近在咫尺而我们的演讲却了无声响。
当我们希望稍稍开口时,
克里姆林宫的居住者站在路中央,
他粗粗的手指像蛆虫一样油亮,
他的话语的重量确有四十磅,
他穿着闪闪发光的牛皮服装,
他的开怀大笑像嘴唇上有只蟑螂。
在他周围是一群脖如鹤颈的丑类,
他把这种半人半鬼家伙的奉承当做儿戏玩耍。
他们吹口哨、学猫叫和哭哭啼啼地诉说,
只有他独自地用他的手指在指指戳戳。
他一点点地扔出马蹄铁似的东西――
公正写在眼晴里、脸上、额头上。
枪毙一词使他的那帮人更加愉悦,
奥塞梯人挺起宽阔的胸膛。
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当天,诗人阿赫玛托娃便从列宁格勒赶到莫斯科,与帕斯捷尔纳克商量通过上层关系进行营救。随后,帕斯捷尔纳克立刻去找《消息报》主编布哈林,气愤地对他说,他不明白怎么会不饶恕这样一位伟大诗人所写的几首不大高明的诗歌,竟然把人抓去坐牢。
布哈林于是给斯大林写了封信,结尾处写道:“连帕斯捷尔纳克也感到紧张。”
帕斯捷尔纳克的确紧张,“因为您知道,现在发生了多么怪异可怕的现象,他们开始抓人;我怕隔墙有耳……”四月末的一天晚上,当曼德尔施塔姆在街心公园向他朗诵这首诗后,他马上说:“我没听过这首诗。您也不曾向我读过这首诗。”――他显然是希望曼德尔施塔姆不要再传播这首诗。“克里姆林宫的居住者”无处不在。
斯大林很熟悉帕斯捷尔纳克――他的父亲曾是少数几位获准出入克里姆林宫并为列宁画像的画家之一,斯大林本人也常常电话约见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对他们的作品作出具体的评判,虽然他这样做常常令作家们胆寒。
“斯大林同志要与您通话。”――帕斯捷尔纳克在闹哄哄的公寓里接过听筒。这一次斯大林谈的不是作品而是曼德尔施塔姆。斯大林说他已下达指示,曼德尔施塔姆的事情将妥善解决。
关于这个电话,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现存的几个版本都是与他比较亲近的人根据他的讲述记录下来的,关键内容也大同小异。阿赫玛托娃的回忆应该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
斯大林问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不替朋友奔走,“如果我的诗人朋友遭到了不幸,我会不顾一切地去救他。”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如果我不为他奔走,您大概还一无所知……”“为什么您不来找我或者找作家组织?”“作家组织从1927年起就不管这种事了。”“可他毕竟是您的朋友吧?”帕斯捷尔纳克一时语塞。斯大林在短暂的冷场之后继续问道:“他毕竟是位大师,大师呀!”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这没有意义。”
……“为什么我们老是说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早就想跟您谈一谈了。”“谈什么?”“谈生与死。”斯大林挂断了电话。
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再试图给斯大林打电话,但“斯大林同志正忙着”,于是他只能给斯大林发了一封信……曼德尔施塔姆虽然被减轻了处罚,但还是被“隔离并保护”着流放了3年。在那段时间里,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又多次去找不停更换的最高检察长替曼德尔施塔姆说情,但那时恐怖已经开始,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1938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年底死于集中营,克格勃档案中这样记载:“一块木板捆在他的腿上,在木板上用粉笔写着他的编号。”
二
曼德尔施塔姆的死无疑使帕斯捷尔纳克感到负疚――很显然,电话之后他肯定也意识到,如果他在电话中不是吞吞吐吐,而是直截了当对斯大林说,曼德尔施塔姆不仅是“大师”而且是他的“挚友”,其结局或许会有所不同。当时,莫斯科流言四起,有人指责他在斯大林面前没有替曼德尔施塔姆说情,后来甚至有人写诗攻击他坑了曼德尔施塔姆,要他对曼德尔施塔姆之死负责,起因恐怕也在于此。
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要在电话中“回避”曼德尔施塔姆,甚至“转移话题”要和斯大林谈谈生与死的问题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真的诗人,正如他的好友,文学理论家、翻译家楚科夫斯基所说,他“是个崇尚生活真实的虔诚信徒”,“真”是他的本质,即便人命关天,他也不会讲假话;而且,真的诗人总是倾向于或者说被规定了将思索引向“形而上”。法国诗人马拉美曾说:“诗是一种紧要关头的语言。”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紧要关头”说的自然也只能是“诗的语言”。
 |
|
《日瓦戈医生》电影海报 |
至于帕斯捷尔纳克提出要谈谈生与死的问题,则与斯大林的“大师”提法有关。因为帕斯捷尔纳克关注的是生命,不是某个人的生命,而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所以他很自然地认为斯大林提出“大师”这个问题“没有意义”。1934年,“他们开始抓人”,曼德尔施塔姆只是一个个案,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和斯大林“形而上”地谈谈生与死的问题了。“我生性就是如此/遇事都要穷本清源……”帕斯捷尔纳克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但是,与斯大林谈论生与死绝对是个错误。被捕前三个月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的曼德尔施塔姆,对此曾不无预言性地写下过这样的文字:“革命本身意味着生与死的较量,它不能容忍在进行革命时侈谈什么生与死的问题……”所以帕斯捷尔纳克一谈生与死,斯大林便撂下了电话――无论在“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层面上,两人都“错位”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处境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只能是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和对曼德尔施塔姆莫名的歉疚。
“看来,你不善于保护同志。”十多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在给女友伊文斯卡娅讲述这段往事时说,斯大林在挂断电话前还讲过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是此前其他版本中所没有的,或许这可以视为帕斯捷尔纳克十多年来的一种自责――如果当时斯大林根本没有讲过这句话。
又过了十多年,帕斯捷尔纳克在回忆录《人与事》中写了这样一笔:
在三十年代中期,在(1934年8月)作家大会召开之前,我的作用被夸大了……
或许他更想说的是,那时他怎么也救不了曼德尔施塔姆,或者说救不了曼德尔施塔姆们(有人估计,死于恐怖时期的作家不少于600人,最多可能达1500人),更不要说非作家们了。
但面对那个曾经活生生的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终究还是难以自圆其说――即便说了,又如何能改变别人对这个电话的现实解读呢?
也许,还是斯大林了解帕斯捷尔纳克。
恐怖时期,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上过黑名单,据说是斯大林的一句话救了他:“不要触动这个天上的人……”
斯大林很现实,而且绝对掌控着“形而下”的现实。当帕斯捷尔纳克提出要和他谈谈生与死的问题时,斯大林看到了这个“天上的人”的天真――也许,只有绝对的“形而下”,或者说只有绝对地掌控着“形而下”,才能直觉到绝对的“形而上”,犹如黑暗与光明因为绝对的反差而灼人心魄。
三
斯大林撂下电话,阻断了生与死的探讨,帕斯捷尔纳克也因此陷入了生与死的困境。
生与死这个问题,帕斯捷尔纳克12岁时便听父亲和作曲家、钢琴家斯克里亚宾争论过,尽管其中“有一半我听不懂”。如今,这个问题竟实实在在地搁浅在了“形而下”的现实上,而他本人却因被斯大林视为“天上的人”没有受到任何“触动”,甚至被推向了天空,和曼德尔斯塔姆们的境遇有了天壤之别,以至他产生了一种无以言说的负疚感。
曼德尔施塔姆被流放后不久,帕斯捷尔纳克便与高尔基并坐在苏联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布哈林在报告中称赞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诗坛巨擘之一”。并当选为作协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几个月后,帕斯捷尔纳克便病倒了,“患了精神障碍症,睡不着觉,生活失常,经常哭泣,总说到死。”很多年以后,帕斯捷尔纳克对这段日子仍记忆犹新,在斯大林去世前两天(1953年3月3日)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回忆起了自己当时的境况:现在“我就坐在18年前(即1935年)认为是死胡同的窗前,那时我面对着窗户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知道”。
1935年6月,帕斯捷尔纳克应邀出席巴黎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当现场翻译、法国作家马尔罗介绍“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一位诗人”将发表演讲时,代表们全体起立,向帕斯捷尔纳克致以长时间的掌声欢呼。而据作家爱伦堡回忆,帕斯捷尔纳克会前提供的在疗养院里写的发言稿,竟然“主要是谈他的病”。
帕斯捷尔纳克病了。
“大清洗”开始了。
1937年2月,诗人尊敬的布哈林被捕,一去无回。7月,他的好友一位格鲁吉亚诗人亚什维里开枪自杀。10月,另一位格鲁吉亚诗人、也是他的好友塔比泽被逮捕并很快被处决。同月,另一位好友、作家皮里尼亚克从家里被带走,从此“失踪”……在帕斯捷尔纳克居住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当时就有25位作家被逮捕。(有人根据1962年出版的企鹅版《俄罗斯诗歌史》作了统计,结果显示,自十月革命以来,流亡异域的诗人平均活到72岁,而一直生活在俄罗斯或重返俄罗斯的诗人,其平均年龄仅为45岁。)
“天上的人”虽然没有受到“触动”,但他变了。楚科夫斯基回忆说。“在战前最后几年里,每次跟他相会时,有一种印象越来越分明,那就是:仍然是原来的帕斯捷尔纳克,但又不是那个人。……他变得沉静了、稳重了、沉思了,而且心软得令人惊奇。他终于从拖延得相当长的稚气中脱身了。”――诗人不再天真。
打击接踵而至。1941年6月,战争爆发。两个月后,帕斯捷尔纳克最挚爱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对此,他深感负疚。因为6年前在巴黎,茨维塔耶娃曾向他征询是否应该回国,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明确的意见。我不知道应当向她提些什么建议,我生怕她和她那可爱的一家人,到了国内,生活会感到困难。这一家人总的悲剧大大超出了我的顾虑。”1939年夏,茨维塔耶娃回国后不久,大女儿阿丽阿德娜即遭逮捕、流放,接着是丈夫锒铛入狱,最后她连谋得一份食堂洗碗工的工作以维持生计的要求都被拒绝了。她给儿子留下了这样一份遗言:“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阿丽阿德娜的爱称)――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绝境。”
对此,帕斯捷尔纳克“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在回忆录《人与事》最后一章“三个幽灵”中,他这样写道:亚什维里、塔比泽“两个人的遭遇,还有茨维塔耶娃的遭遇,是我经受的最大悲痛”。1943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又将这种悲痛和负疚交织着化成了这样的文字:“既然不是坑害他人的人,就不要给他人做坏事……”
其实还有一个“幽灵”,那就是曼德尔施塔姆。他的遭遇或许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最大悲痛”,但可以肯定是其内心深处的“最大隐痛”。帕斯捷尔纳克曾告诉曼达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捷日达,自斯大林电话后,他很久写不出诗;当流言四起,娜捷日达建议他把电话记录下来时,他又表示不愿意……隐痛,只有隐痛才难以言说,尤其是诉诸文字;而这种隐痛如果得不到疏导,将导致手足无措般的“神经失常”――也就是斯大林电话之后没几个月帕斯捷尔纳克得的那种“病”。于是帕斯捷尔纳克只能在不同时期向亲近的、可信赖的人不断讲述那个电话(这些内容大同小异、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的电话记录计有:阿赫玛托娃版、娜捷日达版、吉娜伊达版、伊文斯卡娅版,以及曾为诗人塑像的女雕塑家马斯连尼科娃版等);于是帕斯捷尔纳克只能在回忆录中借着“三个幽灵”将曼德尔施塔姆这样捎带一过:“我对茨维塔耶娃长期估计不足,同样,由于不同的原因,我对其他许多人――巴格里茨基、赫列勃尼科夫、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也都估计不足。”隐痛,让帕斯捷尔纳克陷入了一种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尴尬。
幽灵……“生存还是毁灭”……沉寂。“我成年时代的主要时光都花在翻译歌德、莎士比亚及其他难度大的巨著上了。”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哈姆雷特》的翻译,并由莫斯科艺术剧院开始排演。但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当哈姆雷特的扮演者问斯大林应该怎样理解哈姆雷特、如何演好这个角色时――不排除这是一种“讨好”,现实中很常见、似乎也很智慧很文化的“讨好”,斯大林却作了这样的回答:本来就不应该排演《哈姆雷特》,因为它不适合当代现实。斯大林又一次“撂下了电话”,《哈姆雷特》的演出计划被取消了。
帕斯捷尔纳克和哈姆雷特一样不现实,但生活在恐怖现实中的被动的人们是无法理解诗人的真和天真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坎,正如“上”“下”结合便成了“卡”(qiǎ)字一样――“天上的人”遇到了地上的问题,帕斯捷尔纳克“卡”住了。
四
1945年5月,年届高龄的父亲在英国去世,惊醒了帕斯捷尔纳克:除了他亲历的诸多噩梦般的非正常死亡,生命的自然终结同样不可避免。那一年他已经55岁。次年,他在给堂妹、列宁格勒大学古典语言教授奥丽娅的信中写道:“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我哪一天就会死掉,所以我不能把自己要自由表达真实思想的事搁置到无限期去。……一个人到了30岁,40岁,甚至50、60岁,总不能还像8岁儿童那样生活:对自己的能力抱消极的态度,对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让整个一生不得不在一种乏味的程序中度过。”
就在他父亲去世的那年年底,帕斯捷尔纳克开始构思并创作他称之为“我生存的目的”的《日瓦戈医生》。1946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几乎在“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捷日达:“我想写一部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
在开始创作的最初几年里,帕斯捷尔纳克多次写信给奥丽娅透露自己的创作心迹,或者说某种隐秘――
如今,当关于我的误会和丑闻已经根深蒂固的时候,我反而真的想成为一个人了!我抱着极其愚蠢的想法企图纠正和说明所有这些含糊不清的话和有头没尾的故事。老实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写一部真正的作品。
我在所有人的面前都负疚。可是让我怎么办呢?所以说,这部长篇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证明我也尽了自己的努力。
如果我不能在其中生存与成长,那么我一年也活不下去,我心中的某些东西,我神经的某些部分,几乎是以完整的明确性移植其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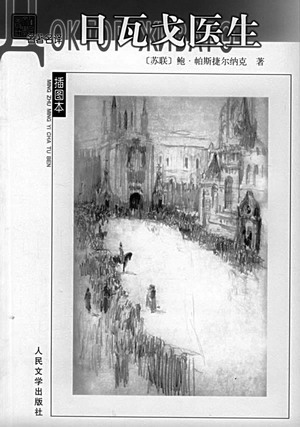 由此,帕斯捷尔纳克将生与死的问题“移植”给了一位“医生”――日瓦戈,他要让这位“医生”来消解世人对自己的“误会”以及他内心的“负疚”,解开那个越抽越紧的心结,冲出那个“卡”。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他“力求使人相信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还活着,他们的时代还存在,而作者却走开了,他躲到一旁,他不存在了……”
由此,帕斯捷尔纳克将生与死的问题“移植”给了一位“医生”――日瓦戈,他要让这位“医生”来消解世人对自己的“误会”以及他内心的“负疚”,解开那个越抽越紧的心结,冲出那个“卡”。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他“力求使人相信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还活着,他们的时代还存在,而作者却走开了,他躲到一旁,他不存在了……”
不仅帕斯捷尔纳克自己“躲到一旁”,甚至连他的“生死对手”斯大林也“不存在”了。1955年秋,《日瓦戈医生》脱稿后,时任苏联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的费定注意到:在这部“从勃洛克写到这场战争”的历史小说中,没有斯大林。
“天上的人”自以为将“形而下”托付给了日瓦戈医生。自己便回到了天上,已经在和上帝交谈了。于是他说:天上没有斯大林。――这并没有全错。
其实,当帕斯捷尔纳克有一天放下手中的笔,“强忍着眼泪,声音哽咽”地打电话告诉伊文斯卡娅,说:“你知道么,他死了!死了!”的时候,他肯定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日瓦戈医生死了,一如曼德尔施塔姆死了,而他还活在地上,甚至连躯体已经僵硬的斯大林也还在地上――生与死的问题仍在帕斯捷尔纳克手中,只要活着,他便难以冲出那个“卡”。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接下来便是国内对他和《日瓦戈医生》的猛烈批判。噩梦般的岁月。渐渐地,他感觉自己就像“书页之间夹着的一片枯叶”。1960年5月30日,一阵夜风掀开书页。枯叶飘飞……
“……甚至生命结束了,我的问题也不会结束。人们将来还会谈论我,最后大家才能承认我,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天上的人”最后时刻看到的是他在“地上的不朽”――不朽,其实很可疑,甚至很滑稽:谁能说他不希望存在的斯大林不在不朽者之列?――帕斯捷尔纳克至死依然“卡”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
五
忽然想到,帕斯捷尔纳克如果遇到的不是“对文学感兴趣”的斯大林,而是列宁(这并不是说他对文学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许就不会这么“卡”住了――
“您该知道,政治――向来是肮脏的东西,您最好不要过问这些事。”当高尔基因友人落入契卡之手而求助于列宁时,后者的回答是那样掷地有声,足以振聋发聩到将高尔基拉回到“形而下”的现实中,因此高尔基虽然也生气,但毕竟没有“卡”住,说起这事还能“大口吐着烟”。
由此看来,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只要在同一层面上(同“上”或者同“下”),纵然是绝对相反的见解,都还能自圆其说,都还有自我圆通的希望,只要想“圆”;但倘若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则无论两者如何靠拢,总是“卡”,而且那个“卡”字会很难看。――遗憾的是,但凡求真的生命便无从躲避这个“卡”。
帕斯捷尔纳克年轻时曾经说过:“我们唯一能够支配的事是使发自内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调。”也许,的确仅此而已,如曼德尔施塔姆。
(摘自《悦读》第7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