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相隔,生死两界,这是人们常用来描述死亡的说法。活人永远都无法见证自己的死亡,然而,恰是自己至亲的死亡,才让我们体悟到上述说法的痛心疾首。就此而言,死亡,永远都是生者的事。据考证,甲骨文中“死”的含义,就是一个活人跪在死者旁边。正如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只有人才有死亡,动物只是生命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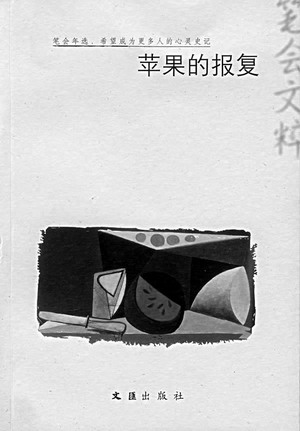 在我看来,作为文化的界碑,葬礼的意义非同小可。首先,它提供了一种情感的慰藉。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是生活中的基本常识。用现代较为规范的语言来说,人除了智商,还有情商。只可惜在当下语境之下,对情商的理解常有变味之嫌,这就是把情商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沟通、交往的能力,或者干脆说,就是一种公关能力。因此情商可以培养、训练,以成为谋事的工具。不过在我看来,真正的情商,或者说情感,乃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本真表达。黛玉为葬花而落泪,悲的对象乃是由落花而及天下所有的生命,这样的情感流露足以打动所有的生者。更何况当失去我们的至爱亲朋,此刻生者对死者无尽的痛惜、思念、追忆、缅怀,若是没有某种形式的葬礼,又该如何宣泄、表达?
在我看来,作为文化的界碑,葬礼的意义非同小可。首先,它提供了一种情感的慰藉。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是生活中的基本常识。用现代较为规范的语言来说,人除了智商,还有情商。只可惜在当下语境之下,对情商的理解常有变味之嫌,这就是把情商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沟通、交往的能力,或者干脆说,就是一种公关能力。因此情商可以培养、训练,以成为谋事的工具。不过在我看来,真正的情商,或者说情感,乃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本真表达。黛玉为葬花而落泪,悲的对象乃是由落花而及天下所有的生命,这样的情感流露足以打动所有的生者。更何况当失去我们的至爱亲朋,此刻生者对死者无尽的痛惜、思念、追忆、缅怀,若是没有某种形式的葬礼,又该如何宣泄、表达?
其次,恰是面对死亡,才有人类情感中某种最为神圣情感的升华――敬畏感的形成。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如一头逼近的老虎,或是席卷而来的洪水,我们只有恐惧,亦即畏;仰望头顶的星空,或是远处的群山,我们或许会拥有膜拜之情,这就是敬。但惟有面对死者,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却眼看着他(她)成为一具躯壳,他(她)的灵性或许已升华至某个地方,此刻,尽管爱恨已去,恩怨不再,但生者对死者所有的情与爱都升华为一种神圣的敬畏之情。我们更为尽心地呵护死者,惟恐他(她)受到伤害;我们更为尽职地恪守曾经许下的诺言,惟恐他(她)受到怠慢。其实我们心知肚明,这样的伤害或怠慢都不属于当下的世界,那当然只能属于一个神圣的境界。是的,正是直面死亡,才令我们升华至神圣境界。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假如人类没有死亡,就不会有宗教;还可补充一句,假如人类没有死亡,就不会有神圣。因为神圣还涵盖宗教。
面对死者,我们的先人或许早已萌生这样的问题:为何他的身躯渐渐冰冷不再温暖我们?有一天这样的事情也会降临于我的身上?生命就是这么回事?这意味着什么?于是,这就有了对生命的意义的沉思。我们最先是通过葬礼来表达这种沉思。正如托马斯・林奇在他的《殡葬人手记》中所说,安葬死者经过那么多的程序,就是要表明,他们曾经生活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别于一块石头、一棵杜鹃花,或一头猩猩,他们的生活值得叙说和回忆。
正是这种叙说和回忆,带来了人类特有的历史感。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会有历史,不管它是刻在有形的物上,还是记在无形的音(口头传说)上。一部史诗或史书,不就是一部关于死者的传说?当然,历史或许不会记载或留下芸芸众生的故事,但众多生者却会铭记他们的至爱亲朋留下的点滴回忆,正是这些生动细节的无处不在,随时随地即可呼之欲出,令死者尽管出了家门,却永远走不出生者的心灵。在此意义上,谁又能说生死是永不相通的两重门?
最后,正是面对死者的葬礼,才令生者有暇驻足倾听来自生命底层的细语:生之无常,死之迫近。生命如同黑暗中的一道闪电,倏忽即逝。生命之根恰恰扎在死亡之土壤中。生命来自虚无,又归于虚无。生之饱满恰由死之虚无所衬托,正如夜空衬托出繁星那样。怠慢死亡,快速打发死亡之过程,其实也就是漠视生命。于是,空虚和浮躁乘虚而入。看来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
面对死亡,我们才会自问:生命是什么?在我看来,生命的过程是一道减法。一旦出生,我们就步步逼近死亡。难怪古希腊哲学家会说,最好是不出生。可惜在很多时候,我们尽做加法和乘法,以为在有生之年,只要累积财富就会积攒幸福。殊不知,生命尽头的最后一道算式是除数为死亡的除法,结局归零。视死如归,我们才能深切体会为何生命是一件礼物,它是上苍的恩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功受禄,从虚无有幸来到这个世界,因而此生无论有怎样的遭遇,我们都理当充满感恩之情。
面对死亡,如果我们能怀有对生命的感恩,对生活的感动,生与死,或许就连成了一个圆圈。
(摘自《苹果的报复》,文汇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