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看到白宫
第一次看到白宫是在1984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在纽约市立学院外的哈莱姆小区做社区组织工作。此时,里根总统正在推行一轮削减学生资助的提案。于是,我与一群
这是一个简短的旅行,得到国会山职员彬彬有礼又草草的接见,这些职员实质上也比我大不了多少。黄昏时,学生们和我便抽时间去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然后再去看一看白宫。我们伫立在离海军陆战队警卫站几英尺远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眼前蜿蜒的过道上满是行人,身后则是汹涌的车流。白宫的优雅恢弘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惊讶的倒是它置身在都市的喧嚣中;我们可以靠近白宫的大门,进而绕到背后去观赏玫瑰花园以及后面的官邸。我想,白宫的不设防表现了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自信。这证明我们的领导人与我们并无二致。他们依然要遵守法律,遵守我们的共识。
二十年后,靠近白宫已不是那么容易了。检查哨、武装警卫、前卫、摄像头、警犬以及收缩的路障将白宫四周隔离在两个街区那么大的范围内。无证小车再不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行驶。在一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也就是我宣誓成为参议员的前一天,拉斐特公园的游人寥寥无几。当小车开出白宫大门驶上车道时,我扫了一眼,不由为昔日情景的消逝而感到一丝凄凉。白宫里面不像你从电视和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光彩夺目。它看上去管理得不错,但是显得有一些老旧,犹如人们想象中的一幢苍老的旧房子。
我得到了一位白宫立法助理的接待,被领进了金器室(Gold Room),大部分新当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已经聚集在这儿。十六点整听到宣布布什总统到达。他向讲台走去,看上去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轻盈而坚定的步履似乎暗示着他胸有成竹。总统做了大约十分钟的讲话,号召这个国家团结起来,话语间伴着几记玩笑,然后邀请我们去白宫的另外一侧用茶点,并与他和第一夫人合影。
我碰巧此时闹肚荒,所以在大部分议员开始排队等候拍照的时候,便向自助餐厅走去。我想起以前与总统的两次邂逅:一次是在议会选举后他给我送来简短的电话祝贺,另一次是总统和我及其他新任参议员一道在白宫用早餐。但是早饭会议时,我发现了他的另外一面。总统开始讨论他的第二任期的安排,主要是重申他竞选演讲的要点――在伊拉克坚持到底和修订《爱国者法案》的重要性等。忽然,好像有谁在后面动了一下开关,总统目光如炬,说话声音有些激动,语速急促,让人不习惯,也不希望人打断。他谦和的态度变得救世主般坚定。看着多数共和党参议员同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此时我注意到权力所能带来的这种危险的隔离感,领会到先辈们设计权力制衡体系的英明。
“议员先生?”
我从记忆中醒来,抬头一看,只见一位年长的黑人站在我面前,他是占白宫多数的黑人侍从中的一员。
“给您换个碟子吧?”
我一边吞了一口像鸡肉的东西一边点点头,却发现向总统致敬的话已跑到九霄云外。我得谢谢我的主人。于是便朝蓝厅(the Blue Room)走去。门边一名年轻的陆战队战士礼貌地告诉我拍照环节已经结束,总统要赴他的下一个约会。但是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总统出现在门口,招手让我进去。
“奥巴马!”总统握着我的手说,“进来,这是劳拉。劳拉,还记得吧,奥巴马。竞选日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视上见过你。美满的家庭。还有您妻子――真是位有魅力的女士。”
“上天对我们家格外照顾,总统先生,”我握着第一夫人的手说道,同时希望自己已经把脸上的面包屑擦干净了。总统转向旁边的一名助手,助手往总统的手上喷了些洗手液。
“来点吗?”总统说,“好东西,防感冒。”
我不想显得不讲卫生,于是也喷了点。
“到这里来一下,”他说,并且把我领到大厅的另一侧。“你知道,”他轻声说道,“我希望你不介意我给你提点建议。”
“一点不,总统先生。”
他点点头。“你的前程远大,”他说,“不可限量。但是我在这个城里呆了些时间了,我要忠告你,做好困难准备。如果像目前这样你被关注得多了,人们就会开始伺机攻击你。你要知道,这种攻击不一定只来自我们共和党,还有你们民主党。人人盼着你出现口误,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自己要小心。”
“谢谢您的忠告,总统先生。”
“不客气。我要走了。你要知道,你我有些东西是共同的。”
“您指什么?”
“我们都与阿兰・凯斯在辩论中遭遇过。那个家伙是个人物,不是吗?”
我笑了。我们一起走出厅门时,我给他讲了一些竞选活动中的故事。直到他离开大厅,我才意识到谈话的时候我的手一直搭在他肩上――一个我下意识的习惯,但是我想,这个习惯为我交了一大帮朋友,更不用说大厅里特勤局的人员了,真是不容易。
最悲惨的一次竞选
 |
|
巴拉克・奥巴马 |
此后事态每况愈下。十月,我为获得一位官员的支持去参加会议,这位官员是尚未向我的对手许诺给予支持的为数不多的党派人士。途中我听到一则广播简讯,国会议员鲁什已成年的儿子于住宅外被两个毒品犯枪杀。我非常震惊,并为议员感到悲痛,我立即暂停竞选一个月。
接下来在圣诞假期中,我去了夏威夷,利用短暂的五天时间看望外祖母,顺便和妻子米歇尔及十八个月大的玛丽亚增进感情。此时,州立法机构就要召开特别会议,就枪支管制法进行投票。但是,当时玛丽亚生病了,无法乘坐飞机,我错过了投票。这项法案没有获准通过。两天之后,我在奥黑尔机场走下夜航飞机,孩子在我身后号啕大哭,米歇尔也不跟我说话。我一眼看到《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新闻,报道枪支管制法因几票之差未获通过,而州参议员及国会议员候选人奥巴马却决定在夏威夷“度假不归”。我的竞选策划人给我打了电话,提到国会议员鲁什有可能制作的广告――一排排棕榈树下,一个男子躺在海滩上的卧椅里,头戴草帽,饮着媚态酒,背景里,有夏威夷式吉他弹奏着悦耳的乐曲,伴随一个画外之声:“芝加哥凶杀率达历史最高,但是巴拉克・奥巴马……”
我打断了他的话,一切都明白了。
就这样,竞选活动未过半,我就从骨子里感觉到我将失败。此后,每天早上醒来,一想到这天我必须微笑着和别人握手,好似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就隐约感到害怕。初选前几个星期,我的竞选稍稍出现转机,在几场报道不多的辩论中我表现很好,我关于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提议得到正面报道,我甚至获得了《芝加哥论坛报》的支持。但是,一切都为时过晚,我赶到庆功宴现场时才发现竞选结果已有定论,我以三十一个百分点落败。
我并非在此暗示政治家的失望和沮丧是独一无二的。我的意思是,多数人失败后,仍能在私下里舔舐自己的伤口,政治家可不一样,他们没有这个特权,他们的失败将被公布于众。你必须面对空了一半座位的大厅诚心诚意发表演说,承认失败;你必须故作坚强,宽慰你的竞选伙伴和支持者;你必须给帮助过你的人打电话表示感谢,还得尴尬地请求他们在你退出竞选偿债时进一步提供帮助。你竭力完成这些事情,但是,无论你用多少大相径庭的理由为自己解释――你认为失败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运气太差、缺乏资金,你不可能不感到,似乎全体公众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你,似乎你不具备必需的品质,似乎你所到之处,“失败者”这个字眼都会从公众脑中闪过。这些感觉是大部分人读中学时就有过的体验,那是一种你暗恋许久的女孩当着她朋友的面用一个玩笑就轻松涮了你,或者一场重要比赛的关键时刻你两次罚球不中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大多数成年人会明智地加以回避。
我记得曾和一个公司老总交谈过,他曾经是2000年总统竞选时副总统阿尔・戈尔的重要支持者。见到我后,他开始讲述选举六个月后与戈尔的一次会面,戈尔正在为他当时刚刚起步的电视事业寻找投资者。
“很奇怪,”这位老总告诉我,“前副总统来过这里,几个月前他差点成为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竞选活动期间,我随时恭候他的召唤,只要他想会面,我就会重新安排自己的日程。但是选举结束后,看着他走进来,突然间我不由觉得与他的会面不过是桩琐事。我很不情愿承认这一点,因为我是真喜欢这个家伙。但是,某种程度上,他已不是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他只是每天到我这儿来寻求资助的众人之一。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简直是处于陡峭的绝壁上。”
陡峭的绝壁,人生的起落。在过去五年中,阿尔・戈尔依然春风得意,影响依旧。我猜想这位老总该又对前副总统的召唤每求必应。但是,在2000年竞选失败后,我想戈尔应该觉察到了朋友出现的变化。戈尔坐在那儿,推广他的电视事业,极力从容地面对逆境。他一定感受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荒唐,他奋斗一生,胜利在握之际,却因为“蝴蝶票”打孔未对准而失之交臂。而他的老总朋友坐在对面,脸上挂着恩赐的微笑。命运就是如此不公,但是那也不能为前副总统改变一切。如同大多数走上公众生活道路的人们一样,戈尔在决定参加竞选的那一刻就明白他给自己带来的将是什么。竞选或许有第二次行动,但是没有第二位。
我和妻子初次相遇
很多人刚认识我太太就立马下结论:她是一位优秀的女人。他们没错――她聪明、有趣而且十分迷人。她当然也很漂亮,但不是那种让男人觉得有压力、让女人感到不安的那种漂亮;那是一种母亲和忙碌的职业女性相结合的内在的美,绝不是我们在杂志封面上看到的光鲜的形象。一些人在某些场合听过她发言或者与她在项目中共事后,会来找我,对她大为赞扬:“你知道我怎么评价你的,巴拉克,但你的太太……哇!”我点头称是,我知道如果我和她共同竞选公职,她一定会轻松打败我。
对我而言,幸运的是米歇尔永远不会从政。“我不够耐心”,她是这么回答别人的。事实也是如此,她实话实说。
我是在1988年的夏天遇到米歇尔的,当时我们都在芝加哥的一家大型法律事务所――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尽管米歇尔比我年轻三岁,但她那时已经是职业律师,她在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哈佛法学院。我那时仅仅在法学院读了一年书,在公司里不过是名夏季实习生。
那是我一生中艰难的转型期。我是在做了三年社区组织工作后进入法学院的,尽管我很喜欢法律,但我仍然怀疑自己的决定。私下里,我会担心这个选择意味着放弃早年的理想,意味着对物欲横流的残酷现实的妥协――一个实在的世界,而不是理想的世界。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想法只会加剧这种恐慌。律师事务所看似很近,但对我那些仍在贫民区工作的朋友来说又如此遥不可及。但随着助学贷款的不断增加,我根本无力拒绝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三个月薪水。因此,我找到最便宜的公寓与人合租一套房间,第一次往衣柜里添置了三套西服,买了一双新鞋,却小了半码,让我足足跛了九个星期。六月初的一个早晨,下着小雨,我到事务所报到,所里安排了一位年轻律师担任我的夏季实习教师。
我已经记不清和米歇尔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内容了。我记得她身材高挑――穿上高跟鞋时和我一般高,非常可爱,举止友善得当。她向我解释了所里的任务是如何分配的,各部门的职责,以及如何计算我们的计费工作时间。米歇尔领我去了我的办公室,又带我参观了图书馆,之后将我交给一位合伙人,同时告诉我她中午与我一块儿用餐。
后来,米歇尔告诉我,当我走进她的办公室时,她感到十分的惊喜。我递交给事务所的是一张在杂货店拍的快照,照片上我的鼻子显得略大(她甚至说,比通常的还要大很多)。当面试时见过我的秘书告诉她我很可爱时,她有些怀疑:“我猜想他们可能只是对任何穿西服且有工作的黑人印象深刻罢了。”但如果米歇尔对我有好感的话,那绝对不是在我们吃中饭的时候。我的确知道,她在南城一座平房里长大,就在我以前工作的社区北边。她的父亲是城市的水泵操作工,她的母亲在孩子们成年之前是家庭主妇,现在是一家银行的秘书。她和她哥哥一样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她当时任职于盛德事务所知识产权部,专攻娱乐法;她说,她以后可能考虑到洛杉矶或者纽约寻求事业发展。
那天,米歇尔忙得连轴转,她告诉我,生活在这样一种快节奏里,她根本没法分神去考虑其他的事情,尤其是男人。但她懂得如何去笑得灿烂和自然,我还注意到她并不急着回办公室。每当我看着她时,我能够从她那圆黑的眼睛里读到点什么――那是一丝跳跃而过的微光,隐隐地透露出她的迟疑,似乎在内心深处,她知道有些东西转瞬即逝,而一旦不去把握,哪怕是片刻,她的所有计划就可能付之东流。这是脆弱的痕迹,它在一定程度上感动了我。我想了解她心灵的这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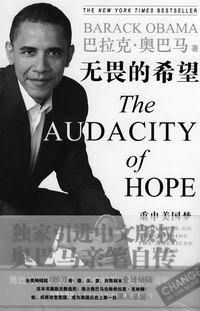 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每天都见面:在法律图书馆,在咖啡厅,或是某次事务所特意为夏季实习生组织的郊游之中。组织郊游的目的是告诉实习生,律师生活并不是无休止地苦读法律文书。她也带着我参加过一两次聚会,并巧妙地掩饰了我没什么行头的窘境,她甚至还介绍我认识她的几个朋友。然而,她拒绝外出与我正式约会。她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她是我的实习老师。
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每天都见面:在法律图书馆,在咖啡厅,或是某次事务所特意为夏季实习生组织的郊游之中。组织郊游的目的是告诉实习生,律师生活并不是无休止地苦读法律文书。她也带着我参加过一两次聚会,并巧妙地掩饰了我没什么行头的窘境,她甚至还介绍我认识她的几个朋友。然而,她拒绝外出与我正式约会。她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她是我的实习老师。
“这个借口糟透了,”我告诉她,“想想看,你给我出了什么点子?你教我如何使用复印机,还是教我该去哪家餐馆用餐?我觉得合伙人不会认为一次约会就严重违反了公司的明文规定。”
她摇摇头说:“对不起。”
“那好,我辞职。这总行了吧?你是我的指导老师,你告诉我辞职该找谁。”
我终于将她说服了。在一次公司组织的野炊后,她开车送我回住所,我提出去街对面给她买“31”蛋卷冰淇淋。在夏日湿热的午后,我俩却坐在路边上享用蛋卷冰淇淋。我告诉她,少年时我曾经在一家“31”冰淇淋店打工,身着褐色围裙,头戴褐色帽子,还要摆酷实在是太难了。她向我透露,小时候曾经有两三年只能吃到花生酱和果冻。我说想去她家拜访,她欣然允诺。
我问她是否可以吻她。我们的吻甜得像巧克力。
(摘自《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法律出版社2008年9月版,定价:4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