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的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米丘林生物科学”恰逢其时,当然要宠冠天下!
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的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米丘林生物科学”恰逢其时,当然要宠冠天下!
在苏联农村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
由政权力量保驾护航,1935―1936年间,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开始直接挑战瓦维洛夫所坚守的遗传学。岂止是瓦维洛夫遇难,遗传学的三位元勋――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以及“孟德尔主义的传教者”、瓦维洛夫的老师贝特森莫不惨遭鞭尸。
1936年12月12日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既宣告了遗传学和农艺学的分道扬镳,更宣告了生物学论战性质的演变――苏联生物学被人为地归属于两大政治营垒,一类被划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便是遗传学;另一类则被称作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米丘林生物科学”――实则是伪科学。
其实,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对遗传学的清剿,并不是遗传学在苏联遭受的第一次磨难。
早在李森科崛起之前的1928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克格勃前身)就曾发表一份关于“沙赫特案件”的材料,指控煤矿工业大批专家里通外国,蓄意破坏,制造事故甚至爆炸矿井及从事其他方面的罪恶活动。有五十多名专家被捕。经过一次特别布置的装模作样的审判,11名专家被枪毙,其他专家被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沙赫特案件”是在科技领域实行镇压的开端。1929年4月,斯大林同志在向苏共十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在科技领域实行镇压的必要性――
在我们的每个工业部门里都潜伏着“沙赫特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被揪出来了,但并不是全部被揪出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破坏活动是当前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这种破坏活动之尤其危险,是由于它跟国际资本相勾结。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清楚表明,资产阶级分子决没有放下他们的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新的进攻。
最高领袖发出了号召,专政机器当然不敢等闲视之。果然,不久又在科技领域揭发出了一批接一批“反苏维埃的”、从事“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批声望卓著的知识分子成了这股镇压狂潮的牺牲品,列宁格勒党委会成立了一个特别的政府委员会对苏联科学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苏联科学院是“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中心”。这个判断葬送了苏联科学院的大批知名学者。三位院士被逮捕,数以百计的研究人员同时身陷囹圄或被开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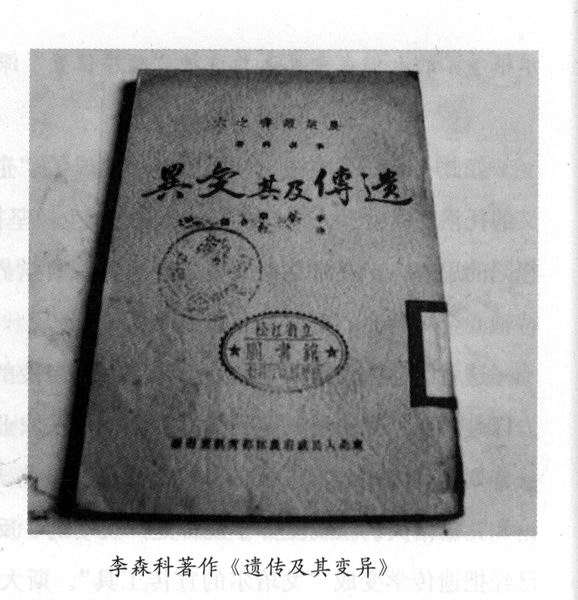
在从肉体上镇压的同时,思想上的清洗更是无孔不入。1929年的苏共十六大就已提出了在科学战线发起“社会主义进攻”的方针,由此引发清查“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急风暴雨。许多本来应该也只有在实验室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提升到阶级斗争的层面,用纯粹的政治手段去处理。一些享有盛誉的学术流派遭到排斥;一些科学泰斗诸如精神病学家贝克托采夫、心理学家考尼洛夫和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都遭到口诛笔伐。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数学家诸如卢津、兰岛、弗克、塔姆等等则被划归“唯心主义者”的另册中。这场风暴一直持续到1934年才告平息。在这场风暴中,经典遗传学备受摧残。拉马克主义者这时已经向经典遗传学提出公开挑战。虽然人数寥寥,但他们理直气壮,恩格斯关于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劳动所起的作用的著名论断――通过食物和活动所获得的特性是可以遗传的――则是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姑且不论纯粹的逻辑推理是否能够解决自然科学问题,单就纯粹的逻辑推理而言,他们没有注意到,恩格斯未曾以任何严格证明了的事实去加强其假说,而且恩格斯的那部作品是在遗传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之前、拉马克主义被实验否定之前写的。所以,即便在逻辑推理方面,他们也是站不住脚的。这批拉马克主义者当时主要集中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所面对的则是几乎全部苏联遗传学家――以共产主义学院自然科学部为其大本营。
论战结果,许多遗传学家被认定在哲学上属于所谓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学派。就是因为这个罪名,那些遗传学家被调离了共产主义学院,苏联实验遗传学学派创始人和群体遗传学奠基人切特维里科夫则被从莫斯科赶了出去,先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然后被赶到符拉迪米尔。流放中的这位遗传学一代宗师再也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等到1955年平反复职时,他已是垂垂老矣,什么都不能做,根本无法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了。1959年他荣获达尔文特别奖,这是德国自然科学院为纪念达尔文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而颁发的奖状。这份殊荣堪称姗姗来迟――获奖时他已是奄奄一息,双目失明。把颁奖的电报向他读了没过几天,他就与世长辞了。
李森科没有投入1929―1934年的那场混战。但那场混战对他却是至关紧要的――正是从那场混战中,他看出遗传学与当局的紧张关系,看出在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遗传学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广阔天地,从而最终选定了“无产阶级金棍子”的人生道路。所以,那场混战的硝烟还未散尽,他就又收罗人马,披挂上阵了。
新的生物学论战肇始于1935年6月在敖德萨植物遗传研究所举行的农业科学院院外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森科帮派与瓦维洛夫学派展开了第一次集中的争论。稍后在李森科和普列津特主编的《春化》杂志上,发起了对遗传学和育种学更为尖锐的攻击,论战由此逐渐发展为全国规模,而在1936年12月12日至27日召开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上达到高潮。这次会议成了苏联生物学史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之后,苏联生物学的两大分支学科――遗传学和农艺学――便分道扬镳了。李森科所独霸的农艺学,再也不可能与真正的遗传学合作,因为真正的遗传学――经典遗传学――已经被当成国家政权的敌人,因而成了专政对象!
在1936年12月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上,李森科和普列津特做了范围广泛的演说。李森科演说的前几个部分是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一般性宣传,然后就转入了对遗传学的全面声讨。李森科强调,有必要对遗传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评价。那么怎样重新评价呢?李森科宣称:遗传是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普遍的内在特性,因此,它不需要一个位于染色体上的、代代相传的单独的遗传系统。他索性不承认有什么基因。李森科气势如虹,令全世界的科学家瞠目结舌。他对遗传学连一个真正学术性的反对观点都提不出来,但这并不妨碍他作出这样的武断结论:“细胞的染色体包含一种与一切其他部分相分离的遗传物质(遗传型)”,他说,这种理论完全是“遗传学家捏造出来的”。
最后,李森科说:
细胞学的光辉成就已经给我们对细胞的形态、特别是细胞的认识做出了很多贡献。我们不仅不否认这一点,而且还充分支持这门科学的发展……但是,我们确实否认这一事实,即遗传学家,还有细胞学家,将能在显微镜下看到基因。使用显微镜有可能、也有必要见到细胞、细胞核和个体染色体中的更详细的情况,但那些都不过是细胞、细胞核和染色体的片断而已,决不是遗传学家用基因这个词所指的什么东西。遗传的基础并不在于某种特别的自体繁殖的物质。遗传的基础是细胞,它发展、演化成一个生物体。在细胞里,不同的细胞器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没有一部分不从属于进化论的发展。
就这样,李森科宣判了遗传学的死刑。至于普列津特在同一会议上的讲话,就更是一篇肤浅的空洞的政治宣传品,更没有说服力了。
斯大林同志的一声断喝,彻底奠定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至高无上的“排头兵”地位,这声喝彩却同时把多少真正的科学家彻底抛到了谷底!随着那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无情地漫卷了整个苏联学术界尤其是苏联生物学界。
但是,真正的科学家的声音,强权从来不予置理。1937年春,斯大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三月全会上发表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肃清托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措施》的著名演说。由此,对遗传学的舆论清剿正式升级为一场政治清洗运动。瓦维洛夫完全失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等要职已被免去,只剩下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这样一个虚衔,实际上他已经靠边站了。但这并非李森科―普列津特们的目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置瓦维洛夫于死地。他们的《春化》杂志在转载了斯大林的著名演说后,刊载了李森科最亲密的战友、该杂志副主编普列津特的一篇大作,把反对“米丘林生物科学”那一派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政治反对派等同起来。强加给瓦维洛夫的罪名愈来愈可怕:“反动派”、“唯心主义者”、“破坏分子”……一张张标签贴到瓦维洛夫脸上,而在风声鹤唳的1937年,谁要是被贴上其中一张标签,那就连上帝也救不了他。
在强化外部围攻的同时,李森科们也加紧了内部策反。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名利的诱惑下,瓦维洛夫的许多研究生不得不易帜,研究所因此愈来愈频繁地发生瓦维洛夫半开玩笑所称的生物学上的“突变”事件――昨天还在瓦维洛夫指导下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年轻人,今天早上一觉醒来便突然宣布,自己是瓦维洛夫学术思想的反对派,要求给他们更换指导老师。不仅如此,为了显示自己立场坚定,他们还必须附和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向敬爱的老师大声地叫骂。
李森科在莫斯科的一次盛大集会上做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春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他宣告:“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农业科学正在超过、在有些部门已经超过资产阶级科学。”李森科毫不掩饰地强调,他的关于科学领域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完全适用于农业科学领域尤其是春化问题――关于春化问题的激烈论战就是科学领域阶级斗争的典型表现,对春化法持有不同见解的科学家都是阶级敌人,即“富农破坏分子”。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动用政权力量、用铁和血来对付他的批评者。谈到这里,他仿佛是向听众呼吁似地说:
同志们:
事实上,由苏联现实所创造的春化学说,在相对来说短短的四、五年内,能够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能够打退阶级敌人的一切进攻(阶级敌人现在还为数不少呢),在这同时,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做。同志们,富农破坏分子不仅在你们集体农庄的生活中出现。这你们是很清楚的。而且,在科学中他们同样危险,同样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和某些所谓的科学家的各种争论中,为了保卫春化学说,为了把这一学说确立起来,我们流了多少血;在实践中,我们还不得不承受不少打击。
请告诉我,同志们,在春化战线上难道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在集体农庄里,富农和他们的教唆者(不光是他们,包括一切阶级敌人)都对着农民的耳朵吹冷风:“别搞什么浸种了。会糟蹋种子的。”他们就是这样骗人的,不管是在科学领域里面还是外面,他们不去帮助集体庄员,而去从事破坏勾当。阶级敌人就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派胡言,讲到这里突然被打断――打断这派胡言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
“好极了!李森科同志,好极了!”
斯大林同志边说边鼓起掌来。暴风雨般的掌声随之席卷整个会场。
斯大林同志的一声断喝,彻底奠定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至高无上的“排头兵”地位。这声断喝却同时把多少真正的科学家――即李森科在演讲中所痛斥的“科学领域里面”的“富农破坏分子”――彻底抛到了谷底。随着那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果然无情地席卷了整个苏联学术界――比上世纪20年代末科学战线上的“社会主义进攻”气势更为壮观的学术界的新的政治镇压狂潮从天而降,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科学家身陷囹圄甚至死于非命。
对科学领域里的“富农破坏分子”的无情镇压,严重摧残了苏联的国力,直接威胁到苏联的生存――在上世纪整个30年代,苏联在科学上的发现和在技术上的突破寥寥可数。
(摘自《苏联遗传学劫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