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刘绪源/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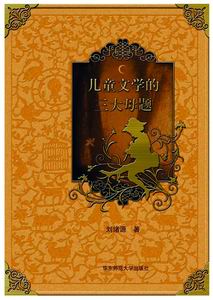 1.1995年的夏天,在上海的
1.1995年的夏天,在上海的
一个关于儿童文学的小型研讨会上,刘绪源先生把他刚刚出版、还带着油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绪源是一位读书方面的杂家。他的阅读兴趣十分广泛,文史哲经、古今中外,丰富驳杂的涉猎,培养了他独特而又精准的鉴赏眼光。同样,当他以“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为论域进入本书的写作之时,他在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甚至更大范围里的阅读积累和鉴赏心得,为书稿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分析基础和文学事实支撑。书中关于伊索寓言、贝洛童话、《明希豪森奇游记》、安徒生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彼得・潘》、《大林和小林》、《洋葱头历险记》、林格伦童话、黎达、汤・西顿、椋鸠十的动物小说(故事)等大量经典作品的分析,既使作者的理论思考和分析获得了来自儿童文学文本事实和历史进程的支持,展现了抽象的学术构架与鲜活的文学生命之间的血肉联系,同时也使作者的文学鉴赏经验和知识库存得到了自然、生动的展示。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本书,也许因此就平添了许多从文学生命的细微处去发现和思考儿童文学学术问题的惊喜和乐趣。
同时,在纷乱的儿童文学现场和多样化的文学思想话语的杂陈中,刘绪源独出机杼,对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作出个人化阐释的学术勇气。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在概述了中外历史上儿童文学、美学等研究领域的分类学状况后认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儿童文学“教育性”与“想象性”的论述,可以理解为一种类型研究。虽然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大都能归入这两种类型中去,但毕竟存在不少例外。黑格尔的“历时性”研究与普罗普的“共时性”研究,都难以避免自身的缺陷,中国现代的儿童文学分类也存在明显的缠夹。作者在肯定了许多大师们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的借鉴意义之后提出,我们也不妨打破体裁、题材、风格、流派这些通常用以划类的界限,打破“历时性”与“共时性”相分离的研究格局,把内容与形式放在一起进行观照,力图作出那种虽或相对朦胧但却尽可能完整的把握。由此作者尝试着用一种新的方法进行类型学的研究,这就是从三个最基本的“母题”出发,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新的划分。这三个母题是,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作者对“母题”概念,作了自己明确的界定。
本书所运用的“母题”概念,居于一个更高的层次。它超越了“题材”概念所包含的具体性和明确性,因而它是一个更笼统的概念。它不再拘泥于作品主人公的身份、作品展开的环境以及故事情节等具体事物。我们说到一个母题,那其实就是指一种审美眼光,一种艺术气氛,一个相当宽广的审美的范围。
作者进一步认为,爱的母题“所体现的,是成人对于儿童的眼光――一种洋溢着爱意的眼光”;顽童的母题“则体现着儿童自己的眼光,一种对于自己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的无拘无束、毫无固定框架可言的眼光,充塞着一种童稚特有的奇异幻想与放纵感”;自然的母题“所体现的则是人类共同的目光,只是这目光对成人来说已渐趋麻木,儿童们却能最大量地拥有它们”。
爱、顽童、自然无疑是刘绪源这本书论述的理论重心,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作者理论思辨和探索的展开过程中,他不断地从正面触及并直截了当地发表着关于儿童文学的一些重大而基本的美学问题的看法。例如,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有三种与此相关的理论:一、儿童文学是教育的,艺术作为手段完全服务于教育目的;二、艺术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作为手段它运载教育内容,作为目的是指载体本身也有审美的价值;三、艺术不是手段,而是审美整体,对艺术品来说艺术审美就是它根本的和最高的目的。儿童文学理论界过去大都赞成第一种观点,这与中国文化“文以载道”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只有极少数例外,如周作人。近年来,许多作家、理论家开始信奉第二种观点,而本书作者则明确表示,他力倡第三种观点。针对以往儿童文学研究中将“教育性”狭隘地理解为“理性因素”这一缺陷,刘绪源则把“教育性”称为“审美中的理性”,并认为,离开审美它们就是作品的外在因素或破坏因素;只有当它们自然流露于作品这一审美整体之中,成为审美情感运行过程的有机部分时,才会在文学中获得自身的价值。他还认为,不是文学的概念大于审美,而是审美的概念大于文学。坦率地说,当我跟随作者在展开关于“三大母题”的思考时,不断读到这样一些关于儿童文学的更为基本的理论问题的论述,我得到的是一种十分过瘾的阅读上的满足感。
2.不久前的一天,绪源给我打来电话说,《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新版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希望我为这一版写一篇“自由的学术批评”,他强调说,“这样会很有趣的”。
说真的,我有一点被他的话所感动。在这个廉价的好话盛行、而真正的批评往往缺席的时代,在普遍的人性中,更多涌起的是喜听奉承之辞的习性的当下,绪源的提议表现出的无疑也是一种十分稀有的精神和个性。同时,我也有一点被他的话所吸引。的确,我认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也存在着某些可能讨论的学术缺陷。
其一,母题的本义是指文学叙事中最小的单一要素,所以才有汤普森庞大、细致的索引系统,并且为文学的分类研究提供了基础。而绪源在书中将“母题”标上了英文“motif”,这表明他所运用的母题概念与西方学者的母题概念是同一的,但是,他同时却将母题定义为一种笼统的概念,一种审美的眼光、气氛、范围,而又未能说明他的母题概念与民间文学的母题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我以为,从论述的学理基础上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漏洞。
其二,母题作为最小的叙事元素,可以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转换、发展出无数作品,因此,母题的功能研究、叙事研究等应该是母题研究的重要领域。而按照本书的界定,母题只是一种笼统的眼光,于是,母题研究所可能具有的无比具体、丰富的内容,反而可能被限制和缩小了。
其三,母题作为最小的叙事元素,它同时总是生成、活跃、保存在特定的文化和叙事传统之中,因此,母题常常也是特定文学的一种叙事“原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母题往往表现着人类共同体(例如不同部落、民族、国家等等)的文化心理或集体无意识,而母题在不同文化母体和群落之间的传播、变换、交融,也构成了文学传播史、交流史和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切入视角,而绪源的研究设定,也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乃至忽略了这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和视角。
事实上,绪源所说的三大母题,严格说起来,我以为他讨论的更像是儿童文学的三大题材领域或三大主题领域。在绪论中,作者将儿童文学的各种作品划为16种题材类型,并认为“只要对上述这十几种类型反复揣摩,那么,很自然地就会摸索到儿童文学的几个最基本的母题。而且我们将会发现,‘题材类型’一旦转换成‘母题类型’,被上述十几个种类所排除或遗漏的作品(包括那些民间流传的‘自然的童话’),都将纷纷归到这些基本母题的麾下”。显然,题材是完全无法归入“母题”(motif)麾下的,那是两个不同的文学能指,其所指、层次、范围等均有不同。更准确的说,作者在这里是把16种题材类型归并成了三大题材领域(类型)。本书的第4章“自然的母题”第1部分为“‘三大永恒主题’与儿童文学的母题”,讨论的是文学艺术中“爱与死以及自然”这三大永恒主题与儿童文学三大母题之间的对应转换关系。这里,作者在引入成人文学进行联系和对比讨论时,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将“母题”概念置换成了“主题”概念,这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作者理论思虑和表达上的某些疏漏和尴尬呢?换句话说,关于儿童文学的所谓三大母题,事实上指的也就是儿童文学的三大永恒主题呢?
3.我还想谈谈绪源先生在本书写作前后所展现给我们的一种恭敬、包容的研究心态和学术伦理。
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已有的学术积累看,《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无疑是一部显示了一定的理论原创能力的著作。令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和写作完成之后,作者始终对自己的观点和著述抱持着相对理性、谨慎、低调和恭敬的学术心态。
了解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批评现状的人们一定都知道,刘绪源是一个特殊的批评个体存在。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当真正理性、犀利、率真、充满个性感悟和体验的批评成为当代儿童文学批评中的稀有现象时,绪源以他的执著、坦诚和天分,成为儿童文学批评现场中那个不时发出真实而锐利尖叫的“孩子”。他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儿童文学》杂志上坚持了9年的批评专栏“文心雕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的一道独特的学术批评风景。因此我相信,他对以自身为对象的学术批评的期待,是真诚而又急迫的,而其间所透射出来的研究心态和学术伦理,则更为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提供了一种有益的专业启示,一笔无形的伦理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