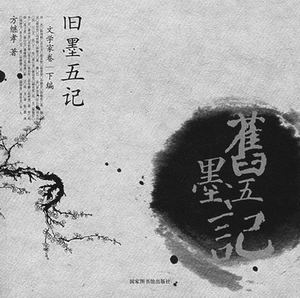
十多年前,启功先生为某次收藏品展览题了两个字“旁证”。启功的意思是这些不起眼的藏品都是历史的旁证,粮票布
方继孝先生的“旧墨记系列”出到第四种(文学家卷)了,我既惊诧他持久的写作能力,也非常羡慕他仿佛用之不竭的藏品。边藏边读边写,这是一条收藏爱好者最理想的康庄大道,也是目下最应倡导的收藏风气。当前的收藏太多乌烟瘴气的东西,炒作盛行,过分强调金钱,不一而足。我入收藏行二十年,现在最厌烦的却是“收藏”二字。收藏界里太少像方继孝这样的既收藏又写作的研究者了,所以也难怪外界持有的偏见。柳和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老档案散失之谜》里指责信札收藏者:“说实话,你不研究出版史或商务馆史,收藏一两封信有何用呢?无非等待升值,待价而沽罢了。可惜一批有用的史料,从此支离破碎,浪迹天涯,再也无法汇集一起加以研究利用。”柳先生的话多有偏颇之见,待价而沽有什么错么?研究和利用并非只是专业人员的专权,方继孝见微知著的写法,靠的就是一两通信札,甚至就是一纸便条。我觉得方先生的书为收藏界争得了一席颜面,收藏家若真的研究起来,他所具有的资料优势,专业人士真的既羡且妒,难免说出一些带醋意的气话。我的倾向是,研究家别老想着像以前似的白使白用别人花大钱搜集的资料;收藏家别老是安于“独得自矜”的低层面理应“化私为公”地写点文章。
信札写作不同于其他题裁的写作,由于作者手中握有确凿的物证,那么“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就应该有严格的自律,绝不能逮着什么写什么。基本的原则应是“扬善隐恶”,尤其是涉及写信者或受信者个人名誉或隐私的内容就不能写。写作也就是做人,我知道方先生的为人,他是绝不会做时下甚嚣尘上的“告密”“卧底”一类文章的,在这方面他是令人放心的和值得信任的。
这本属于“文学家”的《旧墨记》,读起来比之前几本《旧墨记》要来得亲切,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是“于我们亲”。为什么亲,很简单,书中的这些人物对于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鲁迅、陈独秀、周作人、柳亚子、刘半农、郭沫若、张恨水、茅盾、郁达夫、林语堂、叶圣陶、徐志摩、朱自清、老舍、俞平伯、冰心、巴金、钱锺书等等,总计一百位。我们熟读他们的作品,我们熟知他们的生平,现在由方先生从书札这个角度来讲述这些卓越作家的某一件小事,却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另一面,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读者会不断修正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的字写得这么漂亮。”作者展示的“旧墨”也不仅限于书札一门,实寄封、批文、签名本图书、题词、便条、制版凭单、发稿单等举凡带字的一纸一片,皆作为历史的边角料而给予开发使用。我倒是认为专业研究者反而不易接触到这些零纸碎片,他们只对宏大主题有兴趣。
《旧墨记》属于多功能的文化读物,给予读者多项选择,一句话:读《旧墨记》可以有多种读法。当书法读,读者可以从中欣赏到前辈学人的优秀书法(这点尤具现实意义,电脑电传时代,所谓的文化人那一手钢笔字真是不堪入目);当收藏史的片段读,亦无不可;当现代文学史料读,读者完全可以利用作者免费提供的史料线索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旁证。我就是读了后马上用了书里的一篇,来说明那个年代的文化人“草木皆兵”到了何种程度。在《陈翔鹤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一篇中,方先生提供了一张陈翔鹤亲笔写的公函(《文学研究集刊》编辑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事由是,陈翔鹤主编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出版之后,“我们也因失察而至内部送书始被发现”,被发现的是:“发现其中吴世昌的《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中提及的‘柳存仁’(见《文学研究集刊》232页),又名‘柳雨生’,是大汉奸周佛海的部下,是个汉奸文人,日伪时期出席过东京和南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负责过汉奸刊物《疯雨昙》的主编,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纯粹是“杯弓蛇影”,陈他们害怕的不得了,“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在文中提及‘柳存仁’,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我们要求将《文学研究集刊》暂停发行。”正巧我收藏有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杂志,如果不是手迹,我们会以为“疯雨昙”是手民之误,现在有陈翔鹤的亲笔在,一个笑料就成立了。我也正巧收藏有这本1964年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哪天找出来,看看是不是“改正第232页后方能发行”的改正本,要不是的话就珍贵了。历史的荒谬即存在于这不经意的纸片里,由此我们仍可以说前面那位柳先生所云“收藏一两封信有何用呢?”是外行说的话。
我亲眼看过方继孝先生私藏书札的公开展览,现在有些藏品收进书里,仍是那么抢人眼目,这要归功现在的印刷技艺,早年间郑逸梅收藏的书札也出过一本书,印得惨不忍睹,郑老没赶上好时候。这一百位文人中有几位本身即以书法闻名,譬如沈尹默、郭沫若、茅盾、俞平伯、沈从文、柳亚子。可是夏?尊,王统照、周扬、谢六逸的字也极其出色,却是读《旧墨记》的额外所得。要是让我给这些书札排个队的话,最漂亮的倒是王统照1942年的一通小简。不得不说的是,大多数文人的字真不敢恭维,连起码的整齐划一也谈不上。
书里有关稿酬的论述有四处,涉及叶圣陶、胡风、郁达夫、张恨水。我一直认为文人们极少敢于公开议论稿酬,这是文人虚伪的一面。稿酬是他们维持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作家社会地位和个人尊严的物质体现,怎么都那么一致地集体沉默啊。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如鲁迅,不如郁达夫敢于像包括侵占个人利益(如稿酬)在内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作斗争。我也不赞成叶圣陶“不取稿酬”的作法(详见《叶圣陶自动不取稿酬书》),也许叶圣陶的“不取”有着时代的背景,可是我仍要问,自己的劳动除了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也需要得到自己的尊重,“不取稿酬”在某种意义上近乎默认自己的劳动“一钱不值”,但是如果将稿酬捐献给公益事业则又是另一种态度,前提是属于自己的利益应该由自己来支配,也就是说应先“取回稿酬”。
信札手稿里隐秘着太丰富太生动的文化史信息,每一件都是世间孤品,毁掉一件就是一条旁证的灭绝,此事宜急不宜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