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明珂狂称自己的研究范围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但这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中研院”史语所)的研究员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史,因为那也是父亲王光辉坎坷
王明珂狂称自己的研究范围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但这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中研院”史语所)的研究员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史,因为那也是父亲王光辉坎坷1952年,王明珂出生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并在这里一直度过20岁之前的时光。几乎是在父亲的挫折和父母成天的吵架声中度过贫穷而压抑的童年。为暂时忘却家庭烦恼,王明珂高中时曾在眷村子弟组织的“黄埔帮”中厮混。朋友中不乏读完卡夫卡、尼采感到苦闷而去找人打架的,也有书包中经常带着保险套?短刀与新诗集的。混太保、打群架之余,王明珂也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小说,赚一些零花钱。
换过4所高中,考大学时“考的分数乘以2都考不上”,命运的转机发生在22岁服完两年兵役回家后的7个月里。下定决心考大学的王明珂强迫自己每天读15小时以上的书,用半年温习完荒废掉的全部高中课程。一个在台北混黑道的眷村朋友(两年后被敌对帮派砍死在台北街头)来探望,看到王明珂一心向学,只留下一句话:“替我们打溜的(即“混混”)争口气!”1974年,王明珂终于如愿考上公费的台北师范大学。大三时,为了赚生活费,写了“项羽传”,因为小说中的农民起义描写而被“警总”找去谈话。
30多年后,王明珂仍“很感激那些一起走过彷徨少年岁月的朋友们”;仍念念不忘那半年备考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尝试;仍感念父亲“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
眷村家庭大多没有年老长辈在台湾,所以传统中国由邻里宗亲维系的价值观在这里日益松动,眷村生活给王明珂的最大影响就是“叛逆”,“后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是各种典范的叛逆者”。
本科毕业后,教了一年中学,王明珂又考回师范大学历史院研究所读上古史,当时在这里兼课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管东贵先生是他的指导老师。硕士论文“上古的姜、羌与氐羌研究”大肆解构传统定论又给不出新解释,惹得管先生讲出重话:“你的硕士论文可以毕业,可以出版,但是上面不能有指导教授的名字。”王明珂那时年轻气盛:“当然只有我的名字,那都是我的意见。”“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有一群人可以迁徙一千多年仍然是一个民族,民族到底是什么?”写作硕士论文形成的问题意识此后一直影响着王明珂。
不过,力荐王明珂加入史语所的正是管东贵先生。在人才济济的史语所,王明珂最初3年投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稿子,全部未经审查便被退回;自修人类学,但与人类学本科系毕业的同事王道还一交谈,便知道自己没有读懂。那3年,是王明珂求学生涯中非常痛苦的3年。
史语所最初3年的“困学”,却使王明珂1987年至1992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习如饥似渴、如鱼得水。“那几年,整个东亚系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没人教”,王明珂在本系只修了日语,选的几乎都是张光直、汤拜耶(Stanley Tambiah)和Thomas Barfield?James Watson等人类学系学者的课,广泛涉猎英国体系规范的经济人类学?亲属体系?游牧社会?考古人类学和当时流行的族群理论等知识,尤其是广泛阅读了各类民族志。哈佛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们多习惯以其占优势的田野经验来探讨高深理论,王明珂因此改掉了在台湾时空谈理论的习惯。在博士论文后期,王明珂开始研读沟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社会记忆理论,并尝试将其与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
1992年,王明珂摘得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博士帽后返台,获史语所终身聘职。史语所的语言学家孙天心1992年左右就来内地的羌族及马尔康地区研究语言,他后来给王明珂介绍了四川省民委语言办和汶川(威州)师范学校的一些朋友。
1994年夏天,王明珂终于第一次来到内地,从北京一路去往西安、西宁,并在汶川见到了他硕士和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羌族”。
十年间,王明珂做羌族田野调查的时间累计约一年。当汶川大地震爆发时,王明珂格外揪心,但他更清醒地知道:“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2003年至2007年间,王明珂又多次来四川、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考察当代环境与牧业,目前又转向康藏族群与文化研究。
近年,他在内地累计出版了《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楚乡悲歌:项羽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5月;入选《中华读书报》2008年度“十佳”图书)和《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华书局,2009年5月)、《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7月)。此间,王明珂还整理出版了史语所前辈黎光明?王元辉合著的极具民族志价值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原名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
王明珂试图建立一种历史知识,让当下所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对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有深入了解,从而知道如何珍惜及改进社会现实,进而让整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但以“历史记忆”来研究“族群认同”的努力也招致了怀疑,有台湾史学界前辈公开质疑他“历史怎么会是人们想什么就是什么”;还有台湾资深人类学者不承认王明珂研究的是历史人类学,因为“西方历史人类学者没研究这些问题”。
王明珂在羌寨多次听到“毒药猫”(一般指有毒、有巫术的人,多为女性)的传说,他发现这实质上只是人们创造一个内部敌人作为代罪羔羊,以此来化解群体内部的紧张关系(是人类凝聚“我族”的常用伎俩)。王明珂梦想着创造一套完整的“毒药猫理论”,他不惧怕台湾学界各学科的主流威权,宁愿做一个有主动穿越、破坏边界能力的“毒药猫”。
10余年来,王明珂结识了李绍明、汪宁生?童恩正?俞伟超和罗志田、王铭铭等两代内地学人,无形中参与和见证了两岸日益密切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他还有一些小心愿,比如,在机会合适时来大陆高校“指导些学生”;比如,寻访到父亲当年遗散在武汉的亲人。
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仍在于先解决各地的经济开发?分享与社会公正问题。……在社会记忆上,不用去强调各民族的光荣“过去”,更重要的是共创美好的“现在”生活记忆。
问:1994年,您最初是怎么开始来内地做田野调查的?以“台胞”的身份,遇到过什么困难或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王明珂:那时候,两岸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已不那么强,内地正大规模经济开发,所以我算是在那夹缝中溜进来的罢。刚来时,偶然有些地方干部会问我是否想来投资,但当知道我及我的亲友都不是做生意的,他们对我也就没兴趣了。
我的田野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一般,我在每一地都停留不久,一般是四五天就离开,然后往后几年一再回去探望朋友,这样,我到许多地方,对本地人来说都像是来了老朋友。对地方乡长?村长?书记来说,由于我停留短,也不会给他们添麻烦,而且,他们都是以威州师范学校的学生家长(因陪同我去的都是威师的老师)或某人的舅舅?老根之类的身份接待我,这对我的田野研究更是一种便利。
在那十年中,几乎是每个暑期,有时也在过年时,我们一伙人便到处翻山越梁子。那时山中村寨生活封闭、交通不便,来了远方的客是地方大事,加上陪同我的羌族朋友周老师?树全?毛老师?泽元等到处熟人朋友多,所以在每一地方都有让我感动与难忘的事。当然,在那儿跑了一两年后,我的四川话说得可以,这也是个关键。村寨的朋友知道我是台湾来的客,但对我能说四川话毫不感到意外。有一回?周老师以这事问了一个羌族村民。他的回答是,台湾人也是汉人嘛,当然会说“汉话”;原来他们将四川话称汉话,认为汉人说的都是这口话。
问:历史心性、文本、表征与情境、本相、文类、模式化情节和弟兄祖先故事等是您论述的核心概念,您在内地的4本学术著作最终想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学术体系?
王明珂:我透过这几本书想告诉大家,我们所相信的“历史”以及古文献所记载的“历史”,都只是人们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与叙事,甚至是被编造的过去。我希望建立的新历史知识,则是发掘、探索产生这些历史记忆的社会情境本相,以及此情境本相的历史变化,最后对于今日“我”或“我们”在历史中的存在有新的认识。我研究的主题是“华夏及其边缘人群”,也就是今日中华民族中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我希望能建立一种历史知识,让今日所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对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有深入的了解,因此知道如何珍惜及改进社会现实,也就是让整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功能。
在研究方法上,这是更客观精确地将史料当做历史记忆与叙事来分析;并非只是摘取与考订史料中人物、事件的真实性,更探索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产生如此的社会记忆。我分析历史文本的方法,也就是结合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是将文本(历史学的分析对象,也是一种表征)与情境(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本相)对应起来,且更进一步,将文本结构(如正史?方志?族谱等文类)与情境结构(如自古汉系中国人生存其间的帝国?郡县?家族等结构化情境)对应起来。如此我们便能从对历史文本的分析中,了解古代社会情境及其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探讨历史上个别作者在书写间,个别历史人物在行动间,如何顺应或突破?违反种种结构与边界。
历史学家常抱怨,我们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观察现存的社会――由隐藏的社会结构到每个人的情感与意图。而我强调的便是,事实上,已成为过去的一社会之结构与个人,都化为种种密码藏在历史文本之中,我们只要知道如何解码,便能像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样深入观察一古代社会。
最早出版的《华夏边缘》,初步建立以“历史记忆”来研究“族群认同”这样的研究框架。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我从羌族研究中认识“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也因此认识更普遍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历史心性,便是一种影响历史记忆与叙事的文本结构。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我借着对历史心性的认识,重新解释中国史籍中黄帝?炎帝及箕子?太伯等英雄祖先历史,以及一些被视为传说的弟兄祖先故事,也藉此说明华夏及其边缘的形成?发展与近代变化过程。《羌在汉藏之间》是化陌生为熟悉,《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则是化熟悉为陌生;两者共同构成我所称的反思性知识。反思性知识造成有反思及反省能力的个人。
《游牧者的抉择》则讨论“长城”这个古老的华夏边缘之建立与崩解的过程;书中所有单于南下牧马与汉军北伐的历史事件皆被视为表相,产生这些历史表相的人类生态本相则是,长城隔断了人群生存资源的流通。在这书中,我也强调个人的行动抉择能突破边界(包括长城),改变社会现实本相。副标题“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表明这本书是从另一角度思考中国北疆历史,今日满蒙藏族皆为我国族同胞,那么强调华夏英雄跃马长城、北逐鞑虏的历史不是十分荒谬吗?
我们需要一种着重人类生态与长程历史的历史与人类学研究,以此了解各地人群由过去中原帝国及其边裔走向今日中国各民族的历程。然后才能以各宜其地方人类生态的方式,调整政策。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仍在于先解决各地的经济开发?分享与社会公正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以地域为主体,而非以民族为主体。同时,在社会记忆上,不用去强调各民族的光荣“过去”,更重要的是共创美好的“现在”生活记忆;这是美国?加拿大等虽为多民族混杂国家,但基本上并无严重民族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应让每个国人在生活中体认经济?社会?司法等方面的合理?公正,另一方面,所有媒体(当代人社会记忆的重要来源),均应注意本身在此方面应扮演的积极角色。
我在“中研院”服务20多年,从来不会由行政系统知道某重要政治人物将来访;经常是回家后,从电视上知道当日“总统”或“行政院长”来访。
问:1990年代中期以来,您和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陆续有了比较多的业务往来,和李绍明、王铭铭等也有了一定的私谊,对两岸学术同行的治学风格、路数和各自优劣有哪些体会?
王明珂:简单地说,20世纪上半叶以来,新的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后来随学者播入台湾,在台时期又不断有留学生自西方名校毕业返台。因此,台湾各学科的学术传统?师承,以及它们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联结,从未中断且十分稳固。在大陆,有些社会科学学科曾有数十年的中断;重新恢复并自西方输入时,又值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兴之时,过去的学术经典受到质疑与批判,跨学科之新研究领域、议题受重视。
台湾学界,各学科(主要指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由高校课程?论文发表到学术组织?国际交流,都大致系统、制度完整。但各学科各自划界,学科内还分有许多小圈子。其次,长久以来学者对本土现象?资料?问题缺乏反思性研究。
内地方面,由于中断后再重建时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皆尝试追随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缺乏稳固的根源(我是指如1940年至1980年代的人类学),难以建立完整的教学体系。优点是,较不受各学科边界约束,跨学科间的交流互动较多,学术讨论批评之风也较盛行。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多些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
两岸间还有一个社会学术环境差别便是,内地学者与一广大的“读书人”群体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今天在此受访的原因)。台湾自然也有一群“读书人”,但他们的读书品位几乎与台湾学术无关,而是被一些文化人导引至对日本?欧美畅销书的欣赏上。像《中华读书报》这样的媒体,如葛兆光?王铭铭?李零等学者能广为读书人所知,如学术性书籍可被评为年度好书,在台湾都是不易存在的现象。台湾大报《联合报》的“读书人”版最后只剩得一周一个版面,但在今年中还是全面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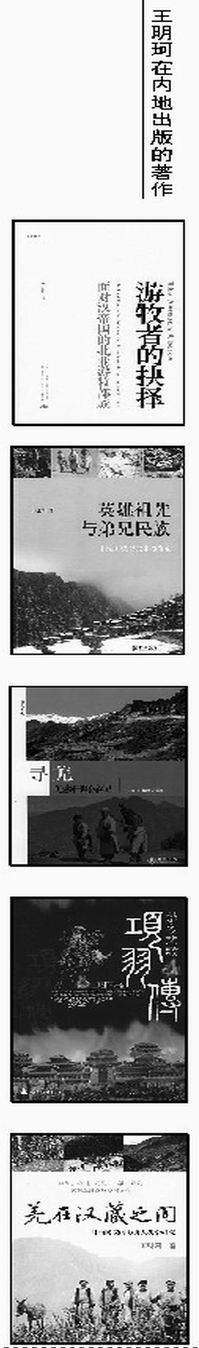 问:也请您谈谈“中研院”和史语所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研究情况。史语所在防止学术腐败方面有何成功经验?匿名评审等制度在实际运转中的效力如何?
问:也请您谈谈“中研院”和史语所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研究情况。史语所在防止学术腐败方面有何成功经验?匿名评审等制度在实际运转中的效力如何?
王明珂:我在“中研院”服务20多年,从来不会由行政系统知道某重要政治人物将来访;经常是回家后,从电视上知道当日“总统”或“行政院长”来访。
历史语言研究所拥有约55位国际著名大学的博士(其中近半数是哈佛及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又享有大量学术资源,目前的研究成绩是远远不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研院”其他各所一样,有十分严格完备的升等?续聘?评鉴办法,学术环境是不错的。然而,我所熟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常过于典范化?精致化,或盲目追求学术新潮以与世界学术接轨,而使得学术完全与现实脱离,也难以产生有创造力的成果。
在我的经验中,史语所并未有学术腐败的威胁。“中研院”倒有个学术伦理委员,近年来也没有处理过学术抄袭案件,这规范完全是建立在学者自重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匿名评审制度相当完备?彻底。有一年,一位审查者给我的文章一个我很难接受的建议与批评,但我只得耐心答复。当时我是集刊编辑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召集人,也是本所集刊编辑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人,但由于制度完备,我不可能知道审查者是谁。
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结合才是学术本分。但台湾近十多年来,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之政治文化风潮下,许多学者以遗传基因学说明台湾人与中国人有基本差别,以语言学说明闽南语和北京话的差别……即使在“中研院”,也有一些学者?院士投身其中。难道这便是学术与现实关怀的结合?
问:我同意您以适当方式介入社会变革、表达现实关怀的主张,但如何守持学术本位?像内地这几年通过《百家讲坛》热播而走红的一些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似乎难以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被尊敬,一些二流学者通过和大众媒体的互相利用得以获取非常多的声望资本。我也听说您的同事王道还先生虽贵为岛内科普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但年年都面临着可能被解聘的危险?
王明珂:恪守学术本分难道只是教教书、写写与世无争只在学术界有争议的文章吗?我认为,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结合才是学术本分。但台湾近十多年来,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之政治文化风潮下,许多学者以遗传基因学说明台湾人与中国人有基本差别,以语言学说明闽南语和北京话的差别,以历史学强调台湾历史始于三四百年前的闽粤移民,以人类学强调台湾的南岛民族特质与平埔族(平地原住民)文化。即使在“中研院”,也有一些学者?院士投身其中。难道这便是学术与现实关怀的结合?若有一天两岸统一,台湾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是否以上的遗传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研究都要重新来过,以证明台湾人便是中国人?
我认为,缺乏反思性的学术介入政治社会现实,对社会?学术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以上许多学者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上所做的所谓“学术贡献”,正应着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一种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偏见――因学者自身的族群?性别?社会阶层等身分认同所造成的认知偏见。这些学者将学术卷入个人的政治见解与活动间,或更普遍地以重量级学者身分支持其学术见解,或以学术领导地位推动有政治目的之大型研究计划,以学术经费?奖金推动具意识形态的特定研究,都是学术灾难。
在台湾,以上学者毕竟并不多。更多的学者,或可能关心社会现实,但他们更热衷于解决宋代科举?明代士人以及某原住民群体的“人观”等问题。这也应着布迪厄指出的另一个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偏见“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将现实世界建构成一个有待被解释的学术图像,以一大套预先假定的理论?方法?原则?词汇来探索描述它,而忘了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这些存在于学科自身内的偏见,也深深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种种表征的理解,或更深化许多原已存在的社会问题。譬如有些学者已指出,人类学的许多田野方法与理论?词汇所创造的知识,让边缘人群(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原住民?少数民族等)持续边缘化。如在国际上,人们关心政治造成的人类不平等?剥削与迫害,但若不平等?剥削?迫害是民族宗教或文化的一部分则无可厚非――这多少是人类学的“贡献”。
我对《百家讲坛》的内容?这些名家出版的书不太了解。然而谈到知识常民化,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将什么样的知识常民化?争论一些历史事实,而造成国家间?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描述一个边缘人群的异类文化,让他们永远存在于现代与变迁的边缘?通俗?有趣,容易让一些观点?价值普及于群众之间;但也常因为通俗?有趣,让包裹着许多偏见的知识广泛传播。
王道还先生在史语所的边缘地位突显了一个学术世界的现实或荒谬:在世界学术圈――以一中国史专题来说,其核心大约是个数十人的团体――中发表?传阅?讨论文章才算是学术贡献,而王君所写的,让上百万民众、学生看的科学普及化文章不能称作学术贡献。
问:说到学术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我又想起《寻羌》中您提到的黎光明,这位传奇人物在史语所1928年创立时即受聘为助理员并迅速开始考察岷江上游的民俗,但1929年从川西回到史语所又迅速离职,1946年竟惨死于铲除鸦片的靖华县长任上(而且他还是回民)。黎光明当年是很不为傅斯年喜欢的,您后来把他和王元辉合著的尘封了74年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整理出版了,您会担心被视为“不务正业”么?
王明珂:我出版黎光明?王元辉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原报告名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一个不具人类学背景的调查者所写的学术报告,是为了突显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特点。黎光明与王元辉描述的是许多活生生的个人;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个人”不见了,我们只见到苗族?藏族。黎光明与王元辉记载一些偶发的事件;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事件”不足为道,那只是浮在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上的一些瞬息即灭的光影。黎光明与王元辉不隐瞒他们在“落后民族”中看见的新事物,但人类学家刻意无视于此,而到最偏远的村庄去寻找一民族的“传统文化”。最后,黎光明与王元辉不掩饰他们对“边疆同胞”的偏见,但人类学者的偏见被学术包装起来,将造成我们今日对原住民或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
在台湾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与人类学界,我早已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了。很早便有史学前辈公开说,“历史怎么会是人们想什么就是什么”――这便是他对“历史记忆”的了解。而资深人类学者也说我研究的不是历史人类学,因为“西方历史人类学者没研究这些问题”。穿梭于各学科边缘,根据我的毒药猫理论,我是有可能成为各学科主流威权心目中的“毒药猫”的,如同RenéGirard著名之代罪羔羊理论中的代罪羔羊。代罪羔羊是无辜的,没有主动能力的,但我宁愿自称“毒药猫”,有主动穿越?破坏边界能力的“毒药猫”。或我也可以自称“武装走私者”,将学术精华由一学科穿越边界带到另一学科中。“武装”是说我认真研读各学科经典之作,那些(代表学术正统威权的)追捕者若无适当学术武装,就别惹我这“走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