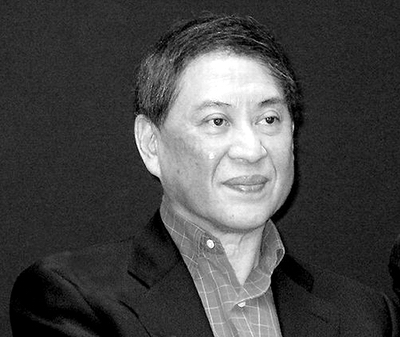
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

白先勇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明媚的阳光下,一位儒雅的长者向我们走来。是的,是白先勇先生,一如传说中的红润的脸庞和亲切的笑容。春天的校园,青春版昆曲,年轻的老人―――一切都那么生机盎然。4月3日下午,北大校园,一家咖啡厅。我们开始了和白先生的长谈。
以青春为号召:《牡丹亭》的校园之旅
记者:作为青春版《牡丹亭》的策划人和制作人,您为什么把该剧的主要观众定位于年轻人?
白先勇:从去年4月在台北首演,到现在《牡丹亭》演出整整一年了。当时在台北演了两轮,观众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年轻人,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冲动,我几乎可以摸得着。在香港,演完了观众有三分之二留下来和我们交流,一直谈到十二点。后来我们到内地演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引起大学生的关注。要只是几场商业演出,放在大剧院里演一演,一般观众看一看,叫好一阵,那样挺简单。但我的目标是必须把它引进校园。我把它定名为“青春版”,有双重目的:一是借这次机会,训练一批年轻演员,因为昆曲演员有断层的危险;二是要培养一群年轻观众,没有观众,戏就会死掉。首先我要从大学做起,然后再扩展到中学,再往外扩展开来。
记者:所以把内地首演定在苏州大学?
白先勇:我们是和苏州昆剧院合作,所以在苏州首演是理所当然的,回娘家嘛。但是最初是安排在了光明剧院。我觉得这样演出意义不够明确,刚好苏州大学来邀请,正合我意。苏大那次有两千个座位,开始我没底,学校说,要不要组织观众?我听不懂,观众怎么还要组织啊?(笑)但是真是没想到票会那么抢手,两三天内一抢而光。苏大的礼堂很旧,是硬板凳,六月份没有冷气,还有蚊子,我一边看一边“噼噼啪啪”打蚊子。我想也许开头是好奇,在这种环境下看九个小时可能坐不住。没想到人一天比一天多,到第三天,两千个位子的礼堂,挤进来了两千五六百人。在浙大也如此,许多人排队抢票。
记者:这次来北大是首进北京高校,之后还要去哪些校园呢?
白先勇:北大演完了,我们就移师北师大,然后去南开,五月去南京大学,月底再到复旦,作为他们百年校庆的一个节目。再下去是同济、交大,但是再往下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所以我恳切呼吁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帮我们一把,下个令啊,协调一下啊。这次如果不是北大的叶朗先生、北师大的曹卫东先生,还有我们加州大学的杨祖佑校长出了大力,我们到大学去,一层一层很艰难的。
记者:那么这次演出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商业性?
白先勇:是有一定的演出费,但比商业的低。北大这次负责演员食宿、宣传费,苏州大学负责运输交通。这次不单是北大,政府也很重视,上次新闻发布会,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于平来了,教育部也来了一位处长。我们演完了就要推向国际,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让他们看看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以昆曲为例:中国文化走向哪里
记者:1957年您考进台湾大学,现在又携青春版《牡丹亭》回到北大。台大和北大说来还是颇有渊源的,您这次来北大是不是很有感触?
白先勇:北大这次演出意义重大啊。首先,北大是近代文化的发源地,一向对文化的走向起着领导作用。另一方面,我是台大学生,我们老校长傅斯年开始就是北大老校长,它把北大传统原封不动搬到台大去,所以北大学生舍我其谁的味道和台大一样,年纪轻轻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笑)我的许多老师像黎烈文、夏济安、台静农都是从北大去的。所以我等于是被北大老师教出来的,我们当年创办《现代文学》就是受北大精神的启发。这次《牡丹亭》到北大演出,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种因缘际会的意味:北大传统培育了我们这一代,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根源,把这个人文传统呈现出来。这些天我时时在想,这样的循回冥冥中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命运,有一条命运的轨迹在那儿。
记者:就是说,《牡丹亭》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个剧目、一个剧种,而与中国文化的命运相关联?
白先勇:是的,今天我回到这儿,来搞这样一个文化运动,是有特别意义的:中国的文化今后到底走向哪里?上世纪有太多的灾难、动荡,我们来不及静下来思考整个民族文化的走向。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静静坐下来,从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等社会学科开始,重新估价我们这几千年的传统文明。现在中国的经济起来了,全世界都看得见中国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除了振兴经济以外,我们的文化呢?我们的古文明能不能再“回春”,这是很关键的。回不来那就危险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埃及啊,印度啊,两河流域啊,一衰落,几个世纪就衰落下去了。现在我们受到的最大的威胁还是西方文化的挑战。你看西方从19世纪开始用他们的科技文化影响全球,取得了霸权。所以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是很有道理的。你要想接受挑战,先得了解自己!我们有什么优点?我们有昆曲!(笑)
记者:就如您说的,“先看看自己后院里的牡丹有多么美。”
白先勇:对,我们得先看自己的花有多美,美在哪儿。昆曲是一种世界性的艺术。我们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有两样东西:一个书法,一个是诗。这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你看今天《唐诗三百首》还是畅销书;无论你走到哪里,看到一幅字画摆在那儿就会肃然起敬。我觉得昆曲就是把书法动作韵律化、舞蹈化,用舞蹈和书法把诗的意境表现出来。把昆曲动作勾画下来就是一幅狂草。说真话,一种艺术形式要超越文化、超越地域很难,但我确信我们昆曲可以。很多看过昆曲的外国人对我说,昆曲美得不得了,真没想到中国古代就有这样成熟的、架构这样恢宏的戏剧,比他们的歌剧历史还要久。
以情为魂:情路探索上的中国文学
记者:您在一篇《我的昆曲之旅》中讲了您和昆曲的很多渊源。但说到底这也和您的文学追求有关吧,文学和昆曲的美是相通的。
白先勇:完全是相通的。都是艺术,都是感动人的东西。特别是昆曲,文学底蕴特别深。我之所以特别迷恋昆曲,很大一部分原因在这儿。比如我写《游园惊梦》,灵感就是来源于昆曲。我刚开始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写,但觉着节奏不对。我就想这样一部小说,应该像音乐一样抑扬顿挫,像笙箫管笛一样有节奏。所以我就用意识流的方式,打破了时空限制。
记者:但是昆曲剧目众多,您却独独钟情《牡丹亭》。
白先勇:因为“情”是《牡丹亭》的灵魂。我的看法是它的境界高于《西厢》。不是说“《牡丹亭》一出,几令《西厢》减色”么。《西厢记》是写实的,而《牡丹亭》已经上升到了一种寓言式的情的层面,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这里面的情已经到了“至”,可以超越生死、感动地狱、打破礼教,到了“情可以胜礼”的地步。《红楼梦》也是讲神瑛侍者和绛珠草的一段神话。所以我说《牡丹亭》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
记者:有论者认为,《红楼梦》完成了《牡丹亭》对情的探索。
白先勇:我想《红楼梦》是情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是把《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合起来了。所以我想,曹雪芹一定受汤显祖佛道思想对情看法的影响很深很深。虽然《牡丹亭》也是歌颂青春、歌颂爱情,可是它底下却潜伏着佛家思想。你比如上面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下面马上惊心动魄来一句“似水流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中国式的伤春悲秋一直贯穿其中。从中国的传统追溯上去,可能从“庄周梦蝶”开始,然后到《枕中记》,一直再到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到《红楼梦》,这里面都是受佛道思想的影响。
记者:《牡丹亭》是戏里入梦,《红楼梦》是梦里入了戏。您的文学也受此影响。
白先勇:是的,有意无意间就受了影响。我想和我的经历有关。我生长在一个历史大转折时代,一切变动如此迅速,如此彻底,真让人感到人生如梦。套用《牡丹亭》的台词就是:“梦中之事,未必非真”哪。这种人生的了悟、洒脱、旷达,我想也是到了一种境界吧。
同一种情怀:从《现代文学》义工到昆曲义工
记者:您曾笑称自己是“昆曲义工”。
白先勇:是啊。不光是我,“昆曲义工”还有很多。这次我觉得最大的安慰就是请来了张继青和汪世瑜两位老师。还有台湾书法家董阳孜,她在英国一个字值十万台币,你看她给我们写了这么多,许多场景都是用她的书法作背景的。
记者:这不是您第一次做义工了。您在台大读大三时就开始和同学一起办《现代文学》,培养了一代优秀文艺家,那时您也是义工。
白先勇:是啊,都是赔钱的。办杂志把房子赔掉了,我把什么都赔得精光。《现代文学》是那时最有名的赔钱杂志,穷得不能再穷。我们自己校对,自己印刷,自己到报摊去派送。
记者:听说印刷厂不给印,您就坐在印刷厂不走。
白先勇:对啊,你不上机开印我就不走。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大三那年,我们说要创办新文学,后来那份杂志真的培养了一代作家:陈映真,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所以我就感觉如果当年不做,也许台湾的文学就缺一块了。
记者:现在做昆曲就像当年做《现代文学》,多年后回头看可能更发现其深远意义。白先勇:现在回头看,确实是培养了一代作家,那时都是二十出头,想想也是青春版啊。现在我年龄也大了,还是春心不死啊。(笑)
记者:您早期的小说就有一篇叫《青春》,现在又回到“青春”这两个字了。
白先勇:是是,台北人讲,你二十岁就写老人的心境,现在反而返老还童,做起青春梦了。
记者:您读的是外文系,却从事中国文学创作;您在美国写了《台北人》,现在又从海外回来做昆曲。可以说,您一直游走于古今中西之间,那您最后的落脚点在哪里?
白先勇:我用杜甫的一句诗来回答:“不薄今人爱古人”。古今中外我都吸收。我觉得现在应该用一种开放的精神来看问题:怎样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融合起来。我喜欢新东西,也不会排斥古人,这取舍之间是学问,就像我们的青春版一样:我们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最后还想对我们的读者说些什么?
白先勇:这次参加制作《牡丹亭》,艰难得不得了。到处化缘到处筹钱,总算为自己的文化做了一些事情。我这只是一个引子,要有政府的帮助、民间的帮助,上上下下都起来才能把这个事做成。我很怕这是个一时现象。万一我做不动了,我希望还有很多人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