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字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碑?碑本来是一个矮的石头,在什么上用呢?是坟墓前面立这么一块石头,原来是为拴绳索好把棺材放到坑里去,这个用途先不管它了。这块石头桩子上刻上字,说明这是谁的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后来又扩大了,这人活着给他立个碑,因为他在这儿做过官,拍这个官的马屁,歌颂他这个官怎么怎
在最初写这碑的人并不一定是什么名家,什么书法家,什么学者,什么官,把它写清楚了,就行了。如果写出来人都不认识,那就麻烦了,就会发生误会,所以碑上的字呢,都是当时正规的字体。到了唐朝初年,唐太宗爱写字,学王羲之,他就写行书字,他可能不大会写楷书字,或者他写楷书字不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写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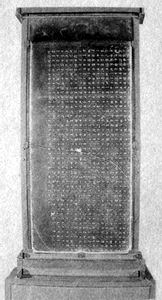 |
|
唐碑形制之一 |
汉代曹全碑 |
后来赵孟?写楷书总带点行书味道,他不是一笔一画死猫瞪眼的那种楷书字,就是六朝的造像那种方头方脑的字。再后来特别是清朝末年,就特别提倡写碑,这个碑就是方头方脑的字。把写碑的叫碑学。打阮元起,就是道光年间,就有这种提法了。后来像叶昌炽,像杨守敬,一直到康有为,都是讲碑字好,是至高无尚的,完美无缺的。其实碑字本身的历史也有变化。原来是楷书字,后来有行书字,有草书字,那碑字并不能纯代表六朝的那些字体。可是他们这些讲碑的,难道碑上字都是标准的吗?那么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他怎么看?《温泉铭》、《晋词铭》又怎么看呢?所以他叫碑学,这种说法本身就不完备,逻辑就不周密。
什么叫帖?帖本来是一个“字条”。北京话叫便条,随便写的小纸条。我给某人写一个简单的小便条,说我什么时候有工夫,咱们什么时候见个面,就这么几句话,这种东西的名称叫“贴儿”,原是给朋友看的,不是郑重其事的,是很随便的。六朝时,流传下来许多王羲之的字条,三行两行,甚至一行也有。有的“帖儿”甚至是给某人写一封信送去了,他要是个大官呢,就在那信的尾上给你批回话,比如人家说请你来一趟,他批“即刻去”三个字,也就是答复那个意见。这种东西叫“字帖儿”。这种东西本来和碑不是一回事,碑本来是让人认识,起告诉别人作用的。字帖呢,无所谓。咱俩你写给我我写给你,两个人心里明白,心照不宣。多草的字,只要这两人认识不就完了吗?
那么帖流传下来就一张纸片,很容易丢失。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字,就搜集王羲之的字。其实打梁武帝那儿已经就喜欢搜集了。零七八碎的条给他裱成这么一个卷儿。由于有这么一个帖,一丈多长,是王羲之写给四川一个地方官叫周甫的信,开篇有“十七日”,写的是日子,今儿个几号,后来管它叫《十七帖》,这就不通了。不是十七张字帖,而是十七日写的帖儿,起头一个名就叫做十七帖。这东西是许多小字条儿,两行也有,三行也有,就打那儿起就有好些帖了。到宋朝有《淳化阁帖》,就是把许多的六朝人的字,汉朝人的字,还有仓颉的字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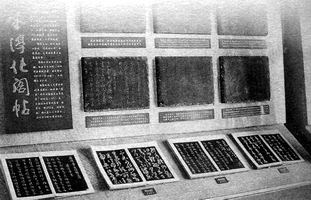 |
|
《淳化阁帖》书影 |
碑和帖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并不一定写碑就是高尚的,就是正统的。有人把碑上字拿来写信,写便条,那非常可笑,一笔一画地写,写了半天,人说你怎么这么费劲呀?还有清朝有个人叫江声,他干脆给人写信都用篆书。给他的一个听差写个条,让听差的买东西去,他用隶书来写;让大师傅去买菜,开个菜单,大师傅说你这是什么菜呀,我不认识。他说隶书呀,就是给你们奴隶们看的字,你们连隶书都不认得,那你不配给我做奴隶、做大师傅。江声就有这样一个笑话。你说我写个便条“请你来一趟”,这五个字都要写得跟六朝造像碑一个样,那算干什么呢?帖本来就是两个人认识,朋友之间,熟人之间互相写,我写得再草,写成密码,只要他认识不就完了吗?当然,写这种帖的草书便条也还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标准、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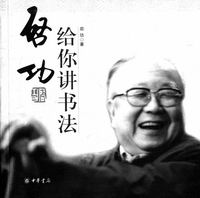 所以碑和帖没有谁低谁高的不同,只有用途上的不同。
所以碑和帖没有谁低谁高的不同,只有用途上的不同。
实用跟个人爱好,跟个人偏好,那是两回事。比如字,我们现在说写美术字,写招牌,我写美术字,那更有自由了,你爱什么写什么,但是写美术字我得先拿尽子、铅笔画出道道来,哪一笔怎样,得画出美术字体的效果。反正我给别人写个信,写个便条,我不能用美术字,用美术字太费时间了。我不反对个人对艺术风格的爱好,我也不反对对于某个古代的某种不成熟的,或者在成熟过程中所经过的某种字体的偏爱,但是我们不能拿我所爱好的一种东西强加于人,说你必须这样才高级,那样就低级。
摘自《启功给你讲书法》,中华书局2005年10月版,定价:1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