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以消费与产业“双升级”驱动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
——评《消费和产业“双升级”协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作者:陈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的两个基本面,二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依赖传统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渐显疲态,消费需求不足、传统产业大而不强、供需结构错配已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协同联动,打通经济循环中的堵点,形成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既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策制定者的迫切需求。龙少波教授的专著《消费和产业双升级协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即立足这一时代命题,系统探讨了消费与产业“双升级”的内在逻辑、协同机制及政策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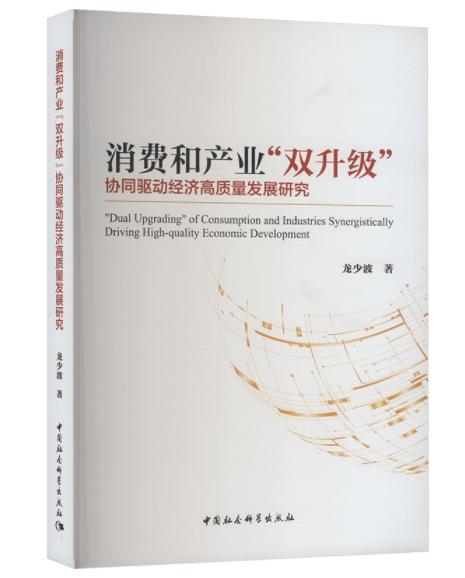
立足问题导向,回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
高质量发展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的重要规律性认识。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创新驱动、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而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正是从需求与供给两侧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消费升级面临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不完善、优质供给不足等现实困难。同时,我国产业升级虽然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仍面临产业链韧性有待提升、创新转化效率有待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有待加快等难点堵点。还有部分领域存在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单兵突进”的现象,消费端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产业端的技术创新与新供给未能及时转化为新的消费需求,二者“脱节”可能导致国民经济大循环存在一些堵点,不利于形成高水平供需动态均衡。
本书敏锐捕捉到这一矛盾,并指出“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并非孤立过程,而应该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系统性工程”。这一判断突破了既有大多数研究重消费或重产业单维升级的局限,强调二者协同能兼顾短期稳增长、中期防风险与长期促改革的多元目标。具体而言,消费升级既能扩大内需稳增长,又能倒逼落后产能淘汰以缓释风险,还能以新需求引领产业升级和供给创新。而产业升级则通过创造新需求进而稳定增长,并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债务依赖进而防范风险,更以技术创新突破来推动体制改革。这种对多元目标兼容的深刻把握,既回应了学术界对“双循环”下供需动态平衡的理论追问,也为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提供了新视角。
彰显理论创新,构建“双升级”协同的理论框架
一是揭示消费和产业“双升级”互动的理论机理。本书提出消费和产业“双升级”的相互影响源于“需求引领创新”与“供给创造需求”的双向良性互动。一方面,消费升级(如居民对健康、绿色、智能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通过市场需求信号倒逼产业技术升级与产品迭代,引领产业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的方向,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如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突破及其对产品的赋能)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催生新的消费模式,形成需求升级和扩张的牵引力。本书通过构建包含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变量的实证模型,量化分析并验证了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互动效应。这种互动需要政策工具的精准适配,短期需通过“以旧换新”等消费补贴政策稳定增长动能,中期需通过化解产能过剩、优化债务结构防范风险,长期需通过完善创新体系、推进要素改革激发增长活力。
二是解析消费和产业“双升级”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消费和产业“双升级”协同可从“市场自发协同”与“政府引导协同”两大层面来实现。在市场层面,价格信号、竞争机制与企业创新是核心纽带,企业通过捕捉消费需求变化调整生产计划,市场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在政府层面,财税政策(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产业政策(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与消费政策(如新能源汽车补贴、消费券)需形成合力,降低政策协同成本并提升政策协同的有效性。在此过程中,各种政策需要避免“单兵冒进”,而应该增强政策取向一致性。例如,若仅靠消费补贴刺激消费而忽视产业端技术瓶颈,可能使得国内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消费者转向购买进口产品并导致需求外溢;若仅加快推进产业升级而忽视对消费升级的积极引导,则可能造成供给冗余。
为此,需要采取科学的宏观政策,包括作用于总需求的稳定政策、作用于总供给的增长政策、可以调整总需求总供给各自结构的结构政策,以“三策合一”加速消费与产业“双升级”,从而驱动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
聚焦政策需求,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操作方案
通过构建“供给提质+需求激活”的双向机制,有助于实现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和供给侧的产业升级,帮助经济更好地形成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一是强化收入分配改革,夯实消费升级基础。加快消费升级需要切实抓好就业增收民生大事,千方百计地改善就业、促进居民增收,以提高消费提质扩容能力。与此同时,需要继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一方面,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低保标准并扩大覆盖范围;另一方面,完善税收调节机制,同时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收入能力。通过降低收入不平等提升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从而提高居民消费率,为消费升级提供持续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改革需与社会保障政策协同,通过提高低保标准的同时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既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又能防范因疾病致贫返贫的风险。
二是聚焦关键领域,推动产业升级提质增效。需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推动供给体系在品牌、质量和个性化上的升级,不断创新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针对产业“卡脖子”问题与低端产能过剩并存的矛盾,需采取“增量突破+存量优化”并行的政策策略。在增量领域,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以颠覆性技术攻关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加大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的攻关投入,培育未来产业新增长点。以颠覆性技术为支撑,塑造数字消费、健康消费、文旅消费等新型场景,助力消费升级。在存量领域,需要做到“有保有压”,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落后产能退出,避免“一刀切”而引发金融风险,同时通过“数字赋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为消费升级培育新动能。
三是完善协同机制,优化政策供给。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关键在于增强各类宏观政策的取向一致性。本书建议中央层面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政策的统筹协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避免“政策合成谬误”带来的效果冲抵。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强化政策的协同联动,放大政策的组合效应,从而有效提升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鼓励地方差异化探索,因地制宜地实现消费和产业的升级互动。例如,东部地区侧重制度革新、高端产业技术创新,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消费市场培育。此外,需重点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基础制度,降低政策协同成本,特别强调政策设计需兼顾“短期见效”与“长期可持续”。例如,通过消费券在短期激活消费的同时,也需同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巩固长期动力。
本书聚焦消费与产业“双升级”协同机制,运用科学理论分析结合严谨实证检验,揭示了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互动规律,阐释了统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内在关联,为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施路径。
